揭秘古诗背后的故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深意解读
这句诗描绘了春天夜晚的惊喜,仿佛春风一夜之间唤醒了千树万树的梨花,让它们盛开,所描述的场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现出大自然的美丽与魅力,整句诗富有诗意和画面感,令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和美好。
在中国诗词枝繁叶茂的序列里,有一脉特殊的题材与类型,既少有文人自怜的悲闷愤郁,也鲜见幽闺伤怀的哀怨凄婉,而是宛若一曲曲慷慨长歌,苍劲雄迈,荡气回肠。它们被称作“边塞诗”,自先秦始,经汉魏兴,至大唐盛。
其中,岑参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他一生两次出关,总共留下了六十余首边塞诗,列于历代骚客之首。特别是第二次西行,对于长期仕途卑微的他而言,不仅是一段功名的高麓,更是一个文才的巅峰。短短一年有余,他便写下了诸多绝世杰作,尤以“轮台三绝”最为卓著,“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等妙句传诵千古。
成就这些诗篇的独特风光与偏陲烽火,都来自北庭——唐朝的六大都护府之一。尽管作为节度判官,岑参仅是文职的副使,但这座西域治所辉映的帝国气韵已足够在一个书生的笔端注入壮志豪情。可惜很快,一切就烟消云散了: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命运急转直下,边军东驰襄援平叛,北庭兵力瞬时空虚;757年,岑参也离开北庭,余生未能复返;766年,河西沦于吐蕃,西域成了飞地,北庭只剩孤忠;790年,七千守军困战而殁,北庭最终失陷。
盛景自此不再,在大唐轰然倒下的暗影里,北庭渐渐沉入历史。
北庭故城遗址俯瞰 供图/郭物
摸清骨架
如今从新疆昌吉的吉木萨尔县出发,向北驱车只需1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昔日北庭所在。合适的月份,岑参笔下“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图景仍旧可以在此得见。只是曾经巍然的唐城全然消逝,徒留几处残垣断壁的土堆散落在旷野之上。
元末明初的战火最终吞噬了北庭。15世纪以后,除了当地民间还依稀记得这里曾有一座“护堡子”,普遍地世人几乎将之遗忘。直到清代乾隆时期,纪晓岚的重新发现才令其回归到了关注的视野。
1768年,受两淮盐运贪腐案的牵连,纪晓岚被革职查办,发配迪化(今乌鲁木齐),在重归一统的新疆度过了几年的贬谪时光。1770年十二月,他奉命为驻军营地选址,勘寻过程中踏足北庭故地,进行过一番考察。而在他离开新疆后的1775年,古城又出土古碑两方,在旗蒙古人、乌鲁木齐参赞大臣、都统索诺木策凌赴现场,辨认出了“金满县令”四字。唐金满县残碑的出土,基本证实了遗存的身份。晚年完成《阅微草堂笔记》时,纪晓岚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述:“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古城……周四十里,皆以土墼(jī)垒成……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土。额鲁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
继纪晓岚之后,儒士徐松也在嘉庆年间到北庭做过探查。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进一步明确写道:“莫贺城又东五十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为后庭县,北庭都护府治也。”
20世纪初,西域探险浪潮兴起,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英国人斯坦因等都先后考察过北庭,日本人绘制了故城草图,斯坦因绘制了故城的平面图。1928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袁复礼也曾到此调查,完成对北庭故城第一次现代学术意义上详细的科学测绘。
不过北庭故城遗址的沧桑面纱真正全面揭开,还要等到2016年。特别是从2018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北庭学研究院组建了联合考古队,正式开启对故城遗址的系统性主动发掘。据考古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介绍,这一次考古行动之所以区别以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严格按照了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念,有规划地、有步骤地系统展开和推进。
依据相关文献,北庭的始建可追溯到贞观时期,唐太宗在平定高昌和招降西突厥后亲自决策设立庭州,到长安时期武则天提升为北庭都护府,又在庭州城基础上进行扩建。但由于缺乏详细记载,今人对于城池本身的了解几乎空白。
具体的考古工作首先从城门、街道、水道等城市框架性节点入手。2016—2019年,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相继被发掘,城门的情况大致得以厘清。而在内城西门前城壕与北门内侧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以及内城北门南侧出土的莲瓣联珠纹唐草地砖,则充分反映了北庭故城的等级,这种瓦当和地砖在唐代非常盛行,因为其中的莲花纹是受佛教的影响,联珠纹最早是从古波斯经中亚传入,被皇家用作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与此同时,通过对城墙夯土的分析,北庭内、外两城的兴建次序也趋于明确:土质纯正的内城城墙基本可以判定是荒地起造,外城城墙多含陶片、木炭等遗存,应在营筑时已有人居住。修正了之前学界一度认为外城可能建于唐、内城大约建于高昌回鹘时期的观点。
2019年,遗址内的水系和道路也得到初步的勘探解剖。由此,北庭故城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两轴四重”:两套指内外两城,两轴指子城南北向的中轴线和整个城池东西向的轴线,四重则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
“考古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之后基本沿用了唐代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郭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左图:北庭故城8号遗址发掘现场
右图: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本版供图/郭物
深入探查
对于城市考古,郭物一直有一个比喻:城垣、街巷、壕沟、水路就像一个人的骨架,而对城市内部的细致探查则是深入肌理的解剖。
因此在对骨架形成一定认知的基础上,北庭故城考古也开始向肌理之下推进。从2019年起,内城西门门洞南侧的高等级建筑遗址、子城西南部大型建筑居址及外城东北部大型官署建筑遗址陆续得到清理,并且这些大型遗址都发现了多次改建和扩建的迹象,表明其在不同时期一直被长期使用。
这些发掘无疑是宝贵的。得益于重要的军事功能,北庭城垣在修筑时便注重了坚固性,因此即使后来毁于战火,残存的格局依然可以保持相对清晰。但城中情况不同,由于荒废的几百年里,故城被庄稼所包围,农民经常在此取土以增加田地肥力,导致遗迹破坏严重,许多地方甚至被挖到只剩下生土层。
所有发现中,尤其珍稀的是几块陶器残片。2021年,它们在子城西南部的10号和11号遗址点出土,其上刻有字迹,经过现场拼对确认为“悲田寺”三字。而且11号遗址点恰恰位于一块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台地之上,台地南部残存着一道夯筑的围墙,遗址还另外发现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很有可能这里曾经就是悲田寺相关的建筑。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发现悲田寺的实物,在此之前它只在文献中有所记载。
“悲田”乃佛教用语,是福田思想下的一个概念。所谓福田,意为可生福德之田,具体方法是通过敬侍供养佛、法、僧等群体为自己种下福德的种子。公元前后,佛教传入西域,福田思想也随之传播到中土,至6世纪衍生出“悲田”一词,强调通过布施贫穷者来培养慈悲心,短时间内即在长安、洛阳等地流行开来。
郭物认为,北庭故城的刻字陶片,可能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有关。悲田养病坊是设置在寺院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今天的免费诊疗所、养老院和孤儿院。其在武则天长安时期最初于长安、洛阳开办,后来渐及诸道诸州,唐宣宗后甚至下沉至县,形成全国性的慈善网络。
“北庭故城遗址出土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说明,即使在西北边疆地区,这一社会救济福利机构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落地,充分体现了唐代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这个寺院位于核心的子城内,可能正是贞观十四年与庭州一起建设的应运大宁寺之所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学者孙丽萍则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在她看来,悲田寺与悲田养病坊是不同的概念,两者虽有联系却不能混用,北庭故城陶器残片上的“悲田寺”所指应为寺院。有唐一代,以“悲田”命名的寺院并非只存在于北庭,吐鲁番出土文书便记载着咸亨年间的安西就曾有过一座悲田寺。依据《资治通鉴》中对唐代寺院“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的记载又可以推断,悲田寺绝非民间小庙,而是归僧官管理之下的有赐额的大型寺院。
不过殊途同归的是,孙丽萍也认为悲田寺是唐王朝管辖西域的有力体现。唐朝力量进入西域之前,除了于阗地区流行大乘佛教,西域其余地方盛行的都是小乘佛教,但随着大量中原士兵及移民迁入,对大乘佛教的需求开始增长,因此悲田寺的修建无疑是一项顺应民心、稳定军心的举措。同时,在新开拓的疆土上造寺立观,也将中原的文化带到了西域,有利于从精神文化层面强固统一。
大唐管辖的一个半世纪里,北庭的确逐渐成为一处佛教重镇,不仅有内地高僧驻锡传法,也与中原一样建有龙兴寺。有唐一代,高宗、武周、中宗、玄宗四次敕令在全国诸州兴修过官寺,此龙兴寺可能即是其中之一。到南宋时,全真教教主丘处机晋见成吉思汗,途经北庭时还曾到访过该寺,其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如是记录:“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1908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在内城西北角的一个遗址点挖掘出土了16块碑刻残块,上存的少量阴刻汉字中也有“龙兴寺”字样。
2016年,游客游览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图/中新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外等比例复制的殿塑像 图/视觉中国
王家大寺
即使大唐远去,此地梵音也未断绝,高昌回鹘崛起之后仍修有佛教建筑。如今的外城南门内侧,即留存着这一时期的一个佛寺遗址。其中一座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的夯土台基是昔日的佛殿所在,外围尚有部分围廊遗迹,东部两端有墩台遗址。基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人工池,可能是掘土建筑高台佛殿后挖出的水池;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可能是佛寺的院墙。基址的西南方位则有一处佛塔遗址。
这并非北庭故城发现的第一个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个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遗址被揭开了尘封的面纱。那是高昌回鹘的王家寺院,专供王室成员奉养佛像之用,因为位于外城西门以西约700米,俗称西大寺。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一支新疆考古队,原计划到南疆选址考古,没承想车辆出现故障。听说吉木萨尔县附近有人在一个大土墩的坡地上挖出了“花墙皮”,于是决定改变行程前去察看,结果不期然解锁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通过对“花墙皮”的清理,100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重见天日。它们题材丰富,笔触细腻,不仅保留了唐代风格,也呈现出当地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幅《王者出行图》,画面色彩以红蓝绿为主,白色和褐色为辅,主要采用了铁线描、游丝描和兰叶描等线描手法,人物面容和服饰着装均显现出民族特征。壁画的下半部有两个大型人物画像,为供养人形象,并以回鹘文题记标注了身份:回鹘王阿斯兰汗的依婷公主及驸马。
高昌回鹘佛寺遗址里的《王者出行图》壁画 供图/郭物
除了壁画,近百尊塑像也随之出土,虽多残损,却难掩生动逼真。尤其是几尊交脚菩萨像,脚尖相对、两腿交叉,带有西域舞蹈的特点,造型十分优美。另外还有一尊巨型的卧佛涅槃像,仅佛足就长0.89米、宽0.3米,通身长度则达到8.7米,体量之大在新疆境内首屈一指。
一北一南的布局则是西大寺的又一个独特之处:南面为庭院,包含库房、僧房、配殿等,北面为正殿,东西北三面筑有上下三层的洞龛。所有建筑都是以大型土坯砌筑于夯土台基之上,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70.50米,东西长43.80米。
不过,规模恢宏的西大寺并没有全部被发掘,为了减少对文物造成不必要破坏,在完成部分配殿及洞龛的考察后,遗址于1980年进行了回填处理。1988年,其作为北庭故城遗址的一部分,入选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的二十年里,整个北庭故城遗址的保护不断升级:2006年,“北庭西大寺遗址保护棚暨博物馆”建设工程启动;2013年,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新疆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遗址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数字北庭”项目启动,利用3D建模、虚拟漫游等技术复原鼎盛时期的街市与佛寺;2024年,《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开展修订工作;2025年,入选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清单。
或许某一天,西大寺遗址将会再次启动考古,以更大的投入、更科学的手段、更持续的周期探索更多的未知,就像2016年以来的故城部分一样。而故城部分同样依然存在着许多待解的谜题,比如城池毁弃的具体时点是哪一年、一次性荒废还是慢慢颓败,比如城内及周边是否可能发现墓地或文字材料……
“北庭故城遗址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只是知道了一点点,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未知的。我觉得,相关的考古工作至少还能做五十年。”郭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郭物《瀚海天山北庭风》,《文物天地》2021年7月;孙丽萍《西域“悲田寺”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十六辑
杂志标题:北庭故城:千年遗存的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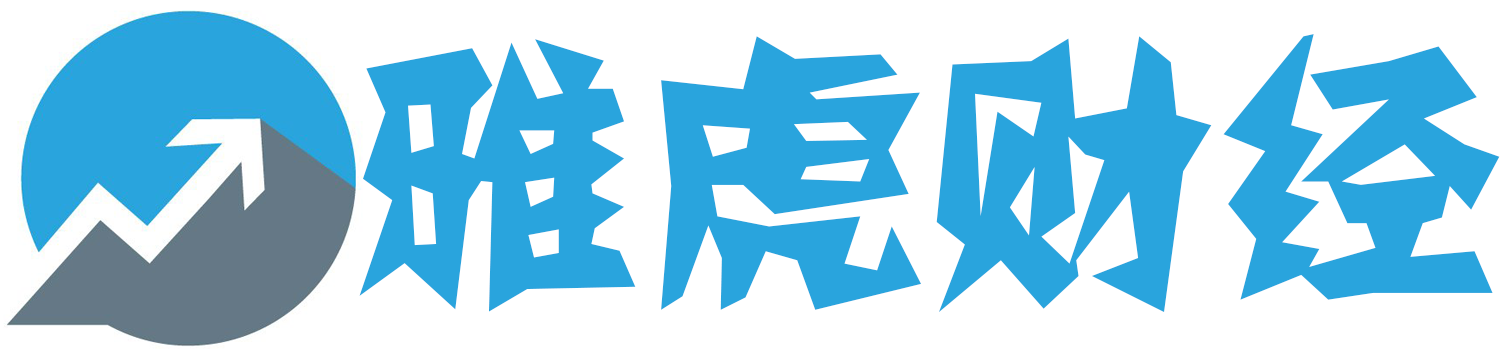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