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灯界显眼包瞩目登场
古灯界的“显眼包”登场,汇聚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这款显眼包以古典灯饰为设计灵感,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其精湛的工艺、优质的材质以及别具一格的设计,使其在众多灯具中脱颖而出,成为古灯界的一股清流,这款显眼包不仅是一盏灯,更是一件艺术品,彰显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从吐鲁番市高昌区出发,一路向西行驶约10公里,就会看到一处遍布院落、高台、佛塔的断壁残垣,在吐鲁番的烈日灼烤下,显得苍凉沉寂。若你能从空中俯瞰,便会发现这废墟在一座岛形台地之上,台地周围是莹莹绿洲,在东边赭红褶皱的火焰山映衬中,犹如一片纤细的柳叶。一道河水从北向南分流绕于城下,故称交河,河上之城便是最早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车师前国”的都城——交河故城。
在一半被山包围,一半被大漠戈壁环绕的吐鲁番盆地中,被河谷冲刷切割出的台地平均有30米高,崖岸壁立又陡峭,如果回到冷兵器时代,这里是绝佳的天然军事要塞,易守难攻。唐代诗人李颀曾说,“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交河故城不仅是唐朝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从交河城出发向北翻越天山,可抵达唐代的北庭,即今天的吉木萨尔,这条道路就是著名的车师古道;而交河城的西北沿白杨河,经唐代的白水涧道,通唐代的轮台城,即今天的乌鲁木齐;西南通唐代天山县,即今天的托克逊,再向西南,经唐代的银山道,便可抵达焉耆,进入南疆。
千年前,城内官衙、寺院、佛塔、民宅、店铺林立,人潮涌动,驼铃声声,而今昔日繁华虽被时光碾为黄土,但城市建筑布局的主体结构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是全球最大最古老、保存得最完好的古代生土建筑城市,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远眺交河故城 供图/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一座在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市
“现在我们就进城了。南城门原来有一个木门,后期因战乱木门被烧毁。”讲解员古丽指着两边城墙上的凹槽说。南门是交河故城的主要出入口,地势险要,有“一人守隘,万夫莫向”的山崖,是当年运送粮草、大军出入的通道。一条宽约10米的笔直中央大路,从南门出发,纵贯全城。
人们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但这座建在近30米高台地上的古城不同。“它是一座向地下掏挖出来的城市,犹如一件巨大的生土雕刻艺术品。”吐鲁番市文物局交河故城文管所所长王建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被称为“压地起凸法”或“减地留墙法”,即在地面事先规划好建筑物的布局,然后向地下挖掘出可用以生产、生活的空间,同时四周保留作为墙体。
为什么使用这种建筑方式,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没有记载。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猜测是,古人因地制宜地就地取材。“吐鲁番自古炎热干燥,元代就被称为‘火洲’,周边地质结构都是钙质黏性土,推测在远古时期,台地就已经形成,先民为躲避部落间战争和野兽的攻击,把家园建在四面河水的台地上。”王建东解释说,当地不盛产石头,正好钙质黏性土坚硬,向下掏挖的建筑冬暖夏凉,于是逐渐营造,有了今天的规模。
数千年前保留至今的奇观,又是丝绸之路的要隘,自然引起西方探险者的注意。从19世纪末开始,俄国、德国等国探险者对包括交河故城在内的吐鲁番众多古迹进行了系统性盗掘,大量壁画、文书、佛教雕像、木器等文物流失海外。20世纪初,当英国人斯坦因考察交河故城时,重要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他只能记录其建筑布局,并在《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描述,交河故城“依崖而建的防御体系令人惊叹”。直到1928年,黄文弼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才第一次对交河故城进行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故城的建筑布局、方式以及沿用年代得到初步判断。
30年前,当考古学者李肖第一次走进交河故城,便被这座奇特的古城震撼了:“城中的大部分建筑,包括宽大的街道,都是从原生土中挖掘出来,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从1992年开始,他参加了交河故城保护修缮工程中的测量及考古发掘,随后又对交河故城形制布局进行专题调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交河故城的一次系统性研究,在此之前,仅有北京大学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给新疆办考古培训班时,组织过试点性教学性的发掘,所获信息有限。
行走在这座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的千年故城,很难不被震撼。它现存遗迹面积约47万平方米,有街巷34条,房屋1300多间,保存完整的有700多间。面对如此规模的古代废墟,出现在脑际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危崖峭壁上的古址始建在什么时候?经历过怎样的世事沧桑?
由于交河独特的建筑技法,这里的地层时代划分“与传统考古完全反着来”。“越向下越晚近,最底下是高昌回鹘时期的遗存,而墙头却发现了仍镶嵌在生土墙壁上石核、化石和用火后留下的炭灰,属于旧石器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李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说明交河台地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人类活动的舞台。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的西域及中亚形势,说明西域地区最近汉王朝西境的是楼兰、姑师,它们虽是“小国耳”,但“当空(孔)道”,地位重要,“邑有城郭,临盐泽”(罗布泊)。这里说到的“姑师”,即“车师”,而车师前部王国的都城,就在“交河”。车师前部什么时候立国,王国都城交河何时建就,历史文献没有留下记录。但对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艾丁湖古墓地等吐鲁番盆地史前时期遗迹的发掘和研究,证明从公元前1000年中期开始,在吐鲁番盆地居住的后来以“姑师(车师)”命名的古代民族,已进入铁器时代,他们世居吐鲁番盆地,至迟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姑师已经立国。
汉武帝元封三年,姑师在汉朝军队的打击下,一分为八,这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了汉文史料中——《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随后,是西汉与匈奴长达30多年的“五争车师”。一直都是这个河心岛主人的车师,如同一片柔弱的柳叶,随着大国的强弱盛衰而摇摆。不过,仅从这五次争夺,就可以看出地处河西通往西域咽喉的车师,战略意义非凡。只要控制了交河城,便可以控制住吐鲁番盆地西、南、北三个方向的交通咽喉,进而牢牢地锁住门户。
战乱时期,交河城的规模很小,通过考古发掘,基本可以断定在汉代,交河城的建筑主要集中于台地南端,也就是今天进入交河故城的大门附近。随着“五争车师”最终以汉军获胜而告终,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府。
公元640年9月,李世民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将其作为统一西域的“桥头堡”,交河城迎来了它在历史中的高光时刻,之后150余年它的城池发展达到了巅峰状态。
2004年,考古学者李肖在交河故城调查。摄影/张永兵
“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
沿着笔直的中央大街一路向北,进入巷道纵横的居民区,如同走入迷宫,两旁皆是连绵不断的高厚街墙,墙上既不开门,也不设窗,建筑均隐没在生土墙后面。人仿佛行走于深沟,一点也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四周寂静无声,强烈的压迫感让行走者无法不怀疑莫测高深的土墙后面,到处隐藏着警惕、敌视的眼睛,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如果居于墙内,则可居高临下,控制内外动向,可以想象昔日城中布防,极为严密。“敌人一旦冲到城里边来,很难施展开他的军队,会被压缩在狭窄的空间,有利于守城的部队再把他们赶出去。”李肖感慨,“这是古人的军事智慧。”
道路两旁皆是连绵不断的高厚街墙 摄影/本刊记者 李静
整个交河城的布局相当成系统,中心大道贯穿南北,北端有规模宏大的大佛寺,并以它为中心构成北部寺院区,再向北还有墓葬区,官署区居中,南部是热闹的居民区。高墙之内的居民区几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单元——坊,坊内屋舍高低错落,庭院交接。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河城有明确的功能区划,特别是城市内中轴线的强化和‘城在南、葬在北’以及‘择中立衙’的布局风格,无不透露出其受到中原城市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典型唐代长安城的形制。”
但如果不仅看城区而且把北部墓葬区等地都包含进来,观察整个台地,居中的则是宗教区。这是东西方城市的最大区别——西方城市中心留给神,东方城市中心留给皇权或代表皇权的官吏,因此,交河同时拥有以宗教建筑为中心的布局特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交河城是中国唯一一个融合了东西方两套城建体系的古代城市。
城内每个坊都有门,但不面对正街,日落宵禁,坊门关闭,待日初再开,这是唐代治城理念。留存至今的交河城,地下庭院及地道形成可追溯至城郭始建的车师时期,地表建筑物主要为唐代遗留。20世纪50年代,新疆考古学者李征曾在遗址内采集到一块莲花纹瓦当,鲜明的唐代风格透示了唐西州时期这里曾有的辉煌。
城市中部的官署区,是交河故城最高的地方。站在官署区高处,干热的风裹挟着沙砾,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官署区正中,有一座宏伟的地下宅院,一走进去,马上从吐鲁番快要把人晒化的阳光下得到了救赎,就连气温都低了几度。“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掏挖生土在地下建房子了吧?到这边来,看看还有什么感觉?”顺着讲解员古丽的指引,在一重门栅外,明显感到内间传来丝丝凉意,里面是一口古水井。栅栏边有三重门遗留下来的凹槽,根据考古推测,这个地下宅院,可能就是安西都护府的住所,后为天山县官署衙门。以水井降温、最为凉快的房间,可能为藏宝阁。
左图:墙上还有三道木门遗留下的凹槽
右图:疑为安西都护府住所的地下宅院
摄影/本刊记者 李静
水井是交河城古代居民的重要供水系统,平日当然可以取水于左右河沟,一旦战争爆发,便只能取饮水于深井。粗略统计,全城共有水井300多口。凭借这些水井,坚守城池,可无断水之忧。1992年至1996年,与交河故城保护维修工程同步展开的考古发掘中,李肖负责的便主要是古井。
在吐鲁番考古,必须适应与内地全然不同的野外环境,“2月严寒,3月狂风,4月就开始了酷热”,盛夏时,吐鲁番的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李肖记得,他每天出发前都要灌一肚子水,然后把几个1升装的大饮料瓶全部灌满,一边干活一边喝,每天仅在城中就要喝掉10升水。这次发掘,让他不仅搞清了交河故城的整个形制布局,还在种种遗存中透过千年时光,“目睹”了那场让交河归于沉寂的惨烈战火。
李肖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清理寺庙古井,他被热得几乎中暑,靠在墙边一边擦汗一边佩服当地技工,他们已经习惯了炙热的高温,不到40度不出汗,下到古井还要穿毛背心。正挖着,井下的技工突然冲李肖大喊:“有人骨头!”李肖赶紧上前,清理出来的先是脚部,随后是躯干,最后才是头部,说明此人是头朝下投入井中。不久,在清理其他水井时又发现了一些人骨,大多是零散残骸,有些甚至是半个脑袋,只有一具完整,姿势和前一具完全相同。经过生物学鉴定,两具完整人骨都为女性,年龄分别约为20岁和40岁。李肖推断,她们很可能是寺庙中的尼姑。那些残缺不全的骨骼所处地层稍微偏上,可能是大战之后,人们在清理废墟时,把这些残缺的尸体扔进了井里。而一些被大火烧成黄黑透红甚至琉璃状的院墙和深深插入地面的箭镞,似乎也诉说着这座古城最后的一页历史。
作为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之地,交河地区曾盛行过源自古波斯的祆教及摩尼教,回鹘高昌时期转变成为佛教圣地,如今交河故城中共有佛教建筑遗迹50多处,可见佛教之兴盛。在李肖看来,寺院拥有太多权力,僧侣众多,而寺院又不交赋税,因此削弱了国力。
明代,吏部员外郎陈诚途经吐鲁番,专程来此瞻仰,留下了一首《崖儿城》(维吾尔语称这里为崖儿城),诗中写道:“沙河二水交流中,天设危城水上头。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那时的交河故城,已是荒冢野墟。因处于吐鲁番干燥炎热的独特气候,使它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废弃后的交河故城,曾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比如关于婴儿墓葬群就有很多猜测。这个大型墓葬群紧挨着官署区,埋葬了200多个不满2岁的婴儿。学者们有诸多推断,例如“瘟疫说”,但干旱少雨的吐鲁番从未有瘟疫的记载,也有“祭祀说”,可是佛教供养多为烧香或供奉食物,并不用人性命供养。目前学界没有特别一致的看法。
2025年6月24日,游客在交河故城大佛寺前祈福。图/视觉中国
“用了10年时间,终于成功”
陶制、筒状,顶部捏制出一位老者形象,栩栩如生,且颇有点动画片里阿凡提的影子,慈眉善目,带点诙谐。如果你在博物馆里看到它,不会想到这是一盏陶灯。因为曾多次被大规模盗掘,交河故城留下的文物不多,现存文物中,“人面陶灯”是颇受关注的一件,有人称它为古灯界的“显眼包”。
人面陶灯 摄影/张永兵
发现它的人,正是李肖,出土地点仍是古井。李肖回忆,1994年把陶灯从西北佛寺的井里拉上来时,技工们还以为这是个炮弹,因为它裹满泥巴,一尺多高,又是柱状,确实有点像炮弹。李肖仔细观察了地层:“没有晚期搅动,炮弹怎么会掉进去?”又拎了一下,“不对,这东西没有金属那么重”。现场拍照、登记完毕,李肖把“炮弹”抱到了交河城下的河畔,用河水洗干净一看,“一个宝贝出来了!”。这不是一盏普通的灯,它是大概1000多年前,繁华的高昌“限量版”,是当时的王室贵族或大城市里有钱人才用得起的精致好物,相当于今天的设计师定制款。
俯瞰交河故城 图/视觉中国
20世纪90年代,在保护修缮的同时进行发掘后,交河故城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再进行考古发掘,仅在2005年又清理发掘了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一些墓葬。2014年,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组成部分,交河故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我们几十年前修缮的了,那时技术条件有限,痕迹挺明显的。”王建东指着大佛寺旁边一面孤墙下角填补的砖石说。被日晒磨砺、岁月淘洗了两千多年,吐鲁番又是强风沙暴的主要灾害区,自然规律是不可抵挡的,但是如何尽力延缓这座生土古城衰老、生病、消亡的生命历程,是如今文物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技手段逐渐应用于交河故城的保护和修缮,但就像王建东说的,早期方法难免朴拙。曾在吐鲁番工作了近30年的李肖感慨,交河故城也算见证了中国土建筑遗址保护技术完善的历程。
“哎,我发明了一种新涂料。”李肖现在都还记得30多年前李最雄的那股兴奋劲儿,那时李最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员,化学专业出身,正在交河开展自己的实验——把一种他研制出的可溶性化学物质(PS)溶解在水中,然后再均匀地喷涂到被保护的建筑物上,喷涂过后的墙壁会变得坚固。他把配好的涂料往实验用的墙上一刷,墙就跟刷了石灰水一样变白了。李肖赶紧说:“这不行啊!你这不把文物本体的样子都改变了!”“没事,我再慢慢研究。”李最雄又回了实验室。
10年后,李肖已经担任吐鲁番文物局局长,李最雄也成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他的PS涂料又来到交河故城。这回,刷过涂料的墙体没有任何改变,泼一瓶矿泉水上去,墙虽然湿了,但是一点泥巴都摸不下来,而没涂过涂料的土墙,变湿后一摸一手泥巴。作为中国石窟和土遗址保护团队的奠基人,李最雄已经于几年前去世,李肖很想念他:“他用了10年时间,终于成功了,现在PS涂料已经在全国推广,拯救了中国众多土建筑遗址。而且这是无机物,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什么伤害。”
除了故城本体的保护,还要确保崖体稳定,同样是敦煌研究院的楠竹加筋复合锚杆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人工骨架”植入遗址内部容易坍塌的崖体和文物本体之内,为其强筋健骨。最近这20年,针对交河故城的多个保护维护工程陆续开工,包括故城不同方位崖体区域的加固,东北佛寺、大佛寺、官署、南门阙等文物本体的修复和保护。正是这些以数十年计的持续维护和修复,为今天和后世的人们留存下一片可以触摸历史的现场。
转眼间,灼烤得人目眩的日头逐渐西沉,当暮色降临,炎阳褪去烈焰,化作温柔霞光铺在这片残垣身上,它就摘掉了时光赋予的面纱,露出昔日西域名城的真容。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人世沧桑变化,沙漠和绿洲曾经将自己拆解为无数文明的基因,却始终是静默的旁观者。
故人的眼泪和离别、昔日战火与喧嚣皆已湮灭,无关枯朽,只留岁月的余声。这一刻,它可以承载一切有关历史与丝路的浪漫想象。
参考资料:《交河故城的形制和布局》李肖;《瀚海行脚》王炳华;《被凝固的唐代时光:交河故城》李敬阳
杂志标题:交河故城 丝路余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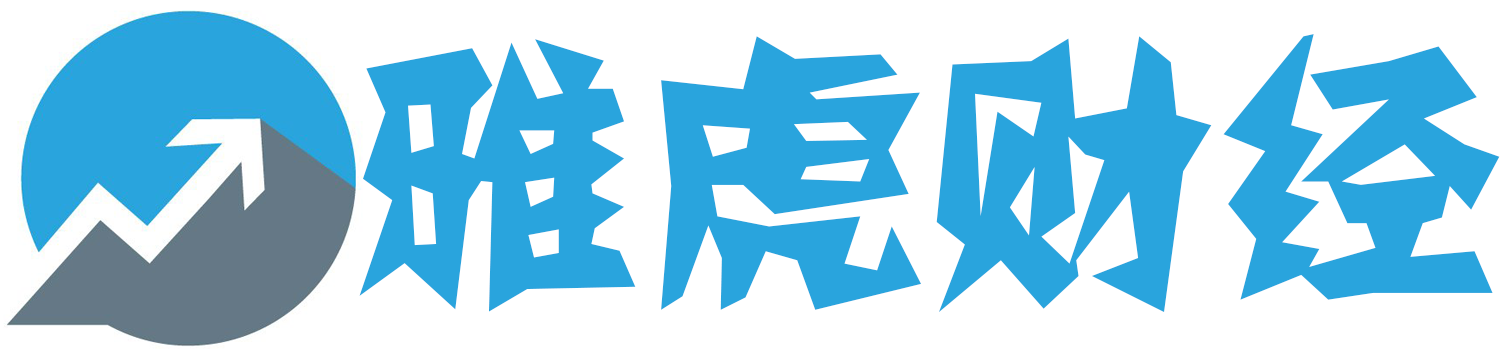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