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这些热词,你将被时代淘汰
如果你还不了解最新的热词,那么你可能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现在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文化日新月异,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不断涌现,跟上这些热词,不仅可以让你更好地融入社交圈,还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化和年轻人的思想动态,保持对新热词的关注和了解,是跟上时代潮流的必备技能。
“制定‘十五五’规划建议,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新变化、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意义重大。”
10月24日,在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说。
全会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如何理解 “十五五”时期的“投资于人”?“十五五”时期要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亟待哪些科技体制改革?基于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3月25日,在东莞的广东拓斯达大岭山生产基地,工作人员在测试工业机器人产品。图/新华
以人为目的
《中国新闻周刊》: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实际上,扩大内需的提法在过去这些年常常出现,未来五年,还应该怎么做?
苏剑: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产能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上,自1997年以来,中国一直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在过去一些年,为了扩大内需,政府采取了许多举措,比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高铁、机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去年的“两重”“两新”政策等。产能过剩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未来几年仍然如此,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是完全正确的。
未来一个时期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我认为,一方面还是要投资于人。对“物”的投资已经没有多大收益空间,再投资可能还会带来亏损,而投资于人,回报永远是正向的,只要人具备创造性,科技发展就没有上限,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也永无止境。所以这也是接下来的方向。另一方面,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这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机制等,让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去消费,有信心去消费。
《中国新闻周刊》:“投资于人”确实是今年的热词,全会也提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国为何在当下将“投资于人”放到重要位置?
苏剑:我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注重对“物”的投资,尤其是对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建设、GDP增长的关注。这些投资在早期阶段具有显著效果。然而到了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物”的投资空间已经逐渐缩小。如今,很多行业面临严重的“内卷”,投资回报率逐步下降,单纯增加物质投资的意义不大。
当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而要实现科技创新,依赖的是高素质人才。因此,接下来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培育。
其实,我国一直在实践“投资于人”的理念,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都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只不过,过去我们没有明确使用“投资于人”这个概念。如今,特意提出这一概念,我认为是国家对人力资本的关注发生了变化。
过去,人被视为生产工具,主要用于创造财富。而现在,我们把人作为目的,把人真正纳入幸福生活的一部分。从更深层次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也需要更加注重提高人的幸福感,因为经济活动和经济本身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服务。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向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福祉转型,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现。
“投资于人”有哪些做法?这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税收、鼓励生育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优化与支持。从政府角度来看,鼓励生育可能会成为政策重点,其次是继续加强教育,我国的各级教育目前在覆盖面上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不适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接下来应该往培养创新型人才方向发展。
如何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新闻周刊》:全会把“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对此应如何理解?
苏剑: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美国曾爆发金融危机,欧洲则经历了债务危机,这些都反映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不足。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自然希望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避免出现系统性或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强调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行业风险、小型金融机构困境,以及当前较大的就业压力等,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新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变化与挑战,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我认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是科技创新。科技不仅能创造新需求,还能带动供给增长。《建议》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意味着,最终拉动需求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只有提供优质的新产品,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从而促进经济健康运行。
《中国新闻周刊》:有关科技创新,全会也有部署,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如何推动下一阶段的科技自立自强?
苏剑:大国博弈的核心在于科技竞争。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科技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这并不是真正的创新。当前,我国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在5G通信、人工智能、航天等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但总体而言,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仍未实现自主可控,要想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避免被“卡脖子”,就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首先要加大科研投入;其次,更关键的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中的核心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既包括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也包括对科研人员的评价。
在国外,对科技成果的评价标准非常简单:市场是否买单。在国内,一些科技成果会拿到各层级政府颁发的奖项,但这些科技成果对经济究竟能起到多大拉动作用,对社会发展究竟有多大贡献不得而知。相反,真正能够创造实际价值的科技成果,未必能拿到奖项。总结来说,当前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行政色彩较为浓厚,亟待改革。
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同样需要改革。行政部门在评估高校科研水平时,看重的是高校拿了多少国家课题,高校继而如此考核教师。但问题在于,申请课题只是获得科研经费,这本质上是在考核科研投入,真正应该考核的是科研产出——能否发表高质量论文,能否转化为专利和现实生产力。在我看来,目前这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浪费了教师时间精力,也造成资源错配,让真正需要经费的研究人员反而得不到支持,这些是需要改变的。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科研创新环境,首先要让科研人员放松下来。目前许多高校实行“非升即走”,几年内发不出论文就会被淘汰。生存危机倒逼年轻教师拼命发论文,但是文章质量实在堪忧,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学术造假现象。但话说回来,高校的科研评价机制介于行政与市场之间,客观性确实难以平衡。如果取消“非升即走”,又可能出现教师躺平不作为的情况。目前我认为至少可以从科创企业入手,为科创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把科创企业打造成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中国新闻周刊》:全会部署“十五五”时期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前,我国面临制造业外移的压力,如何定义“合理比重”?你认为“十五五”时期应怎么应对这种外移压力?
苏剑: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多大,这个问题没有固定标准,不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主要取决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如果分工足够细,那么有些国家可以专注服务业,有些国家可以专注制造业。就像国内一样,北京等大城市完全可以专注服务业,制造业比重可以很低,其他省份可以专注制造业。
制造业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涉及大国博弈,二是吸纳劳动力。在国内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有些制造业是需要外移的,同时我们要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技术升级的方式降低劳动用工需要。接下来需要做的事,依然是升级制造业、鼓励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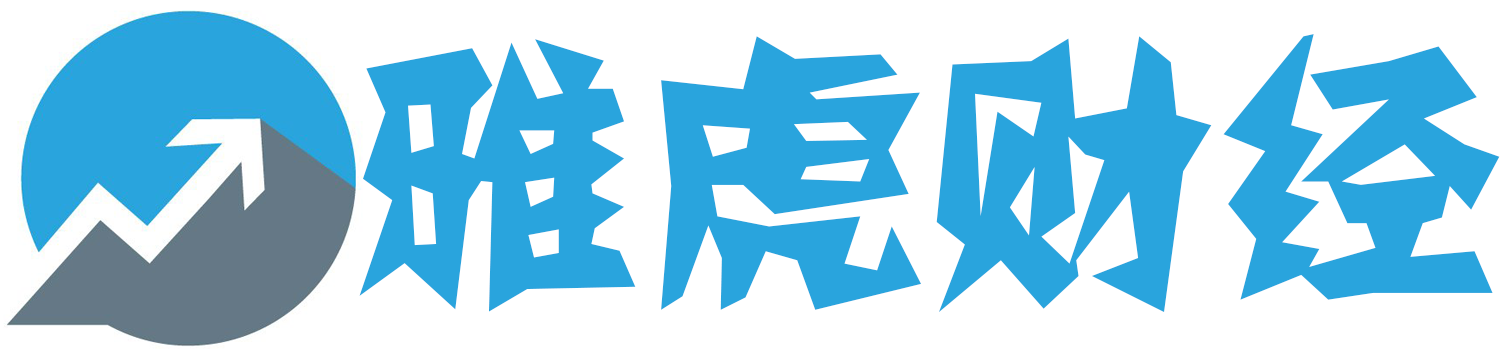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