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送别仪式今日举行
今日送别杨振宁先生,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卓越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敬仰,杨振宁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离去让我们感到惋惜,但他的成就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思和怀念,同时也祝愿他安息。
10月24日上午9时,杨振宁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杨振宁一生都在追寻对称性,虽然他正是因为发现了对称性的破缺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他35岁。
2025年10月18日12时00分,杨振宁因病在北京逝世。17天前,他刚过完103岁生日。他的好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9年年底,杨振宁曾因摔倒而住院,2023年后,其健康状况进一步下滑。今年9月下旬,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
杨振宁的“关门弟子”翟荟回忆,10月18日中午,当他赶到医院后,杨振宁“安详平静地离开了,一如往日的从容”。
杨振宁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物理圈之外,少有人知的是,他因诺奖而知名的宇称不守恒并不是其最有分量的成就。他在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可以排在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必将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类似的影响。”这是1994年美国科学成就鲍尔奖给他的颁奖词。
杨振宁足够长寿,他的同代人——那些划过20世纪物理星空的绚烂人物,大多已去世,杨振宁几乎是最后的见证者,与他一起落幕的,还有现代物理的黄金年代。
杨振宁 摄影/张沫
寻找“统一”
杨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上帝也是吗?
物理学家泡利并不相信。1957年1月17日,他激动地在一封后来广为流传的信中写道:“我要下一笔很大的赌注:实验一定会得出对称的结果。”他指的实验,是为了验证杨振宁与李政道1956年6月发表的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杨和李是对的,二人还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获得了诺奖,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宇称不守恒的结果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它破坏了自然界最优美的法则——对称定律。
当地时间1957年12月11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音乐厅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中)在领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右)向他们鼓掌致意。 图/视觉中国
所以,为什么是杨振宁?
要弄清楚这一切,先要从他对对称性的沉迷说起。杨振宁非常强调科学的品味(taste)。他认为,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taste,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这种风格又决定他的贡献。“物理学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与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
杨振宁的taste最早产生自西南联大时期。1938年,16岁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力考入了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2万多名考试者中,他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
杨振宁西南联合大学准考证。图/清华大学网站
联大物理系对杨振宁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吴是他的学士论文导师。杨振宁后来回忆,1941年秋天,吴大猷让他去研究《现代物理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在数学群论于物理学的美妙应用中,杨振宁开始对对称性产生兴趣,而他的硕士论文导师王竹溪则将他引向统计力学——数学与物理的优雅交汇之处。
1945年11月,杨振宁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他赶上了粒子物理的黄金年代,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和一个全新的领域共同成长。后来,他描述道:“20世纪物理学真正的辉煌之处,在于对一些源自人类文明之初的重要基本概念——空间、时间、运动、能量以及力——的深入理解。这带给我们的,是对自然的一种更加优美、更加微妙、更加精准,同时也更加统一的描述。”
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提出前,物理学发生过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力学革命;第二次是电磁学革命;第三次就是相对论革命,爱因斯坦把时间、空间和引力都统一起来。
随着粒子物理的发展,物理学对宇宙与人类本源认知的拼图已逐步凝练成四块: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到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期间,20世纪物理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把四种力统一起来,爱因斯坦想要通过广义相对论达成这一“终极目标”,但他失败了。
受“统一”的感召,杨振宁想要寻找一个“普遍的原则来描述不同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最初,研究并不顺利,杨振宁1947年写给联大好友黄昆的信中用“幻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但杨振宁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他曾总结科研成功的三个必要条件:洞察力(Perception),坚持(Persistence)和力量(Power)。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中骐对此深有体会。马中骐是杨振宁晚年重要的合作者,2009—2011年和杨合作署名发表了5篇论文。2021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马中骐说,杨振宁的特点是一旦脑海中有了清晰的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达成目标,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不停地尝试,直到走通才会停下。“他经常在算稿邮件中说,虽然计算过程可能还有问题,但结果一定是对的,然后以三个感叹号作结。”
1947年到1954年,杨振宁又尝试了3—4次。直到1954年,他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遇到了同样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学结果”。
这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杨振宁在寻找的那个“普遍原则”。它将除引力之外的三种力统一在一个包容性框架下,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出对现代物理影响最为深远的标准模型。
复旦大学物理系特聘教授、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天文系荣休杰出教授吴咏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20世纪20年代基本粒子时代开启,到70年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完成,短短不到50年,人类对万物尺度的认知再次向微观跨越了10亿倍。“这一快速跨越的实现,杨先生的规范场理论功不可没。”
“一只鸟的贡献”
在杨振宁看来,所有真正伟大的物理理论都是“造物者的诗篇”。在题为“杨-米尔斯”的诗篇中,只有一句诗: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
这是杨振宁物理生涯中最重要的论断,也是他一生思考的凝缩。马中骐说,坚持背后,杨振宁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他对物理世界本质精准的洞察力。
1984年9月24日,是马中骐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第一天,杨振宁当时在这里的理论物理所担任所长。他向杨振宁汇报访学计划,一方面继续做磁单极理论方向的博士论文题目,另一方面深入研究Levinson定理。“杨先生听后对我说,磁单极理论当然可以做,但只是跟着别人后面做而已,Levinson定理就不一样了,它是量子力学中的基本问题。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重要的问题。”
这句话后来成了马中骐一生的座右铭。不过,什么是“基本问题”,就像武林秘籍的神秘口诀一样,每个物理学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受父亲杨武之影响,杨振宁的理解是数学式的。
杨武之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留美归来的数学家,1929年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回忆:“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哈代和赖特《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斯派赛《有限群论》中的许多空间群插图……1938年到1939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四十年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在杨-米尔斯方程中,杨振宁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描绘了对称性。“奇迹的奇迹,数学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他说。
杨振宁的物理学家密友弗里曼·戴森将科学家分为两种类型:鸟与青蛙。鸟在空中翱翔于我们大多数人毕生所面对的琐碎问题的雨林之上,使用能统一思维的概念;青蛙生活在泥土之下,只能看到附近生长的花朵。戴森认为,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是“一只鸟的贡献”。
但鸟不是凭空飞起来的,杨振宁站在两位前辈的肩膀上。一位是爱因斯坦,另一位是德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外尔,他引入了一种特殊的对称性,但只停留在电磁相互作用上。杨振宁则在此基础上推广到更一般的形式。
马中骐解释,外尔相当于把麦克斯韦方程“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论证了一个已有结论”。但很多物理学家捕捉不到这一方法背后隐藏的深刻逻辑,杨振宁却立刻看到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荟是杨振宁回国后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杨振宁曾对他说,你要是真正懂一个物理理论,就要能对它作出推广。“一个理论,如果真的能推广,就要提炼出这个理论中最本质的东西。”
这揭示了杨振宁通向“基本问题”的重要路径。戴森对杨振宁有一个经典评价:“保守的革命者。”杨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了想,觉得他是很有道理的:我重视传统,通常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
吴咏时认为,西方文化语境下,“保守的革命者”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保守强调的是“不极端”,但要做到不极端是很难的,因为要分辨、选择性地接受旧东西。
也就是说,当杨振宁像鸟一样飞过物理学的广阔天空时,他不只望着远处的地平线,也会像青蛙一样认真低头俯瞰地面的每一个细节。杨振宁实现了二者间的平衡。他的这一特点深受老师恩里科·费米的影响。当杨振宁1949年申请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时,费米对他说,在那里不要超过一年,因为“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
杨振宁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所有去石溪分校拜访他的学者,都一定对他办公室里占据了一整面墙的巨大柜子印象深刻。马中骐说,柜子上是一排排的抽屉,按照年份放着杨振宁研究过的各类问题的资料与算稿。每次有人向他请教,他都能立刻精准锁定对应的抽屉。“他的记忆力极好,脑子里装了大量别人的技术与研究方法,供他随时调取。我后来才理解了他说的力量(power),更是要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
杨振宁曾用一个数学式子(D+E+F)/3来描述自己的风格,其中D代表狄拉克,E代表爱因斯坦,F代表费米。对于这三位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大师的品味,他也有过精确而优美的形容:狄拉克是“性灵出万象”、爱因斯坦是“深广”、费米是“稳健有力”。他自认为是各取三人的三分之一。
1955年,物理学家杨振宁与理查德·费曼。图/视觉中国
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杨振宁?
相信“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的杨振宁,却率先提出:弱相互作用中,时空对称性可能存在破坏。正如他身上保守与革命兼具的特点一样,他总是能在相互矛盾的概念中找到一条最均衡的道路。
儒家君子
杨振宁坐在台下。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美国,正在举办一场关于“高能物理未来”的座谈会。快要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发现观众席上的杨振宁,立刻请他讲几句话。杨振宁缓慢地说,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他说完后,现场没有人讲话。这是1980年。会后,一位中国的年轻人要和他辩论,杨振宁说,我不和你辩,但请记住,我所说的话对你的将来,比对我的将来重要。
直到2016年,杨振宁仍坚持他的这一想法。再度引发争议的观点来自他对中国建设大对撞机的公开反对。这是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家努力了几十年的宏大计划:通过粒子之间的高能量碰撞反应,观测粒子的性质。在希格斯粒子2012年被发现后,新一代大对撞机作为“希格斯工厂”,有望补上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
但杨振宁不看好这一方向。他的反对理由从未变过:花上百亿元的成本建大对撞机,去押注高能物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这件事“性价比太低”。中国的多数高能物理学家并不赞同这一点。
多位接近杨振宁的物理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争论背后的核心矛盾是对物理学发展方向的选择差异。杨振宁一向的观点是,做研究就要进入一个“有发展的领域”,他常对年轻人建议,最好选择“没有人耕过的菜园子”,然后才可能“挖出不少新东西”。高能物理几乎所有能影响到整个“拼图”的重大理论成果,都诞生在1980年前,包括对希格斯粒子的预测。因此,在杨振宁看来,这个“园子”太陈旧了。但这种选择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务实,这是非常中国式的选择。
“杨振宁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深深的烙印。”朱邦芬指出,在杨振宁眼中,物理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泰勒、费曼、奥本海默等,是天才,但行事咄咄逼人,有时为求成功不择手段;另一种如费米、周光召与米尔斯,具有君子之风。杨振宁更推崇第二类。
杨振宁曾和人讨论,决定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应保守还是激进”,他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国家利益要高于团体利益;第二是要奉行中庸之道,不走极端。
杨振宁有很重的家国情怀,这不仅影响着他的物理选择,更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成长于中国最震荡的20世纪,终于在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他回忆称,当客机穿越国境线时,他从空中首先看到的,是“离开中国前生活的城市昆明”。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正式退休。朱邦芬透露,这时,他就说过多次想要彻底回国。但当时,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因病需要在美国治疗,他不得不为此将回国计划推后三年,直到2003年底,在夫人去世一个多月后,杨振宁为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一段的终点:清华园,他童年成长的地方。
对杨振宁来说,全职回国后,最重要的已不再是自己做研究,而是为中国培养一批真正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学科人才。他参与了国内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创办,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高研中心”),后改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1997年6月2日,高研中心正式成立,对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杨振宁任名誉主任。朱邦芬是中心成立后被引进的第一个教授。他回忆,虽然杨振宁是名誉主任,但中心的几个基本原则都由他参与讨论并最终确定:第一,人员要精干,教授职位都是终身制,每个位置都要精挑细选,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则都是非固定职位,以始终保持机构学术的活跃;第二,必须提供足够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不限定具体研究方向,也没有经费、论文和项目的压力;第三,要有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给高研中心选择最合适的人才,杨振宁每次都仔细研究候选人的学术资料。“有一次,一个候选人履历很好看,在美国获得过重要的科学奖,但杨先生看了他的所有论文后否决了,他说,原来的工作做得很好,但这几年不够活跃。”朱邦芬说。翟荟形容,高研院的招人模式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
一位不愿具名的接近中心的物理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多年来,高研中心始终能维持“以学术为先”的纯粹文化,排除各种外部杂音,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实现了运行资金的独立性,而不是主要从学校或政府拿钱。其中的关键来自杨振宁一力促成的基金会。
高研中心成立后,杨振宁立刻开始筹款,他以个人名望和人脉在中国香港和北美分别注册了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了100万美元。也是在杨振宁的劝说下,很多朋友也都捐了款。此外,他还把自己每年100万元薪资的部分用于中心。据了解,基金会目前约有1500万元。“这笔钱至少够中心再维持几十年,保证中心人员的薪资待遇基本可以与国际接轨,而且一个老师不参与任何国家项目也可以在这里活下去。”前述学者说。
所有杨振宁身边的人都评价,他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他没有一些天才常有的脾气或傲慢,待人接物平等,有君子之风。
让马中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1年春节。为了推进研究,初一一早,杨振宁就发来邮件表示想邀请物理学家吴大峻一起加入合作。但那天白天,马中骐忙于过春节,没及时查阅邮件。“直到晚上才打开电脑,发现杨先生就这样的小事,已和另一位合作者管习文几次沟通,表示一定要在马中骐表态后才能向吴大峻发出邀请。在杨先生眼中,每个合作者都是平等的。”
晚年的杨振宁仍有着极强的好奇心与旺盛的生命力。他90多岁时,还经常深夜给翟荟发一些算稿,思路清晰。97岁之前,他经常和妻子翁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四处旅行,探索天地。翁帆回忆,85岁前,杨振宁还喜欢亲自开车“上山下乡”,亲友都劝他,可他乐在其中。
杨振宁和翁帆还有一个“杨-翁Studio”。朱邦芬说,杨振宁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夫妻出去旅游,朋友到家里做客,以及生活中遇到任何他觉得值得记录的事情,他都会自拍自剪,还要自己配乐。有一次,朱邦芬带两岁的小孙子去杨振宁家做客,杨振宁看小孩子不声不响但眼睛总在转着,于是拿起镜头,过几天,朱邦芬收到一张光盘,里面是杨振宁为他小孙子拍摄的两分钟视频,其中很多特写镜头。“他能观察到非常细微之处,我小孙子的眼睛总是转来转去的神态我平时都没怎么注意到。”朱邦芬说。
1929年,杨振宁住进清华园时才7岁。他人生的起点在清华的科学馆,这栋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小楼从正门进来,左手第三间,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的办公室。现在,这里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在地。
杨振宁常说,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圆。他特别喜欢诗人艾略特的两句诗: “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杨振宁用一生追求物理学的对称性之美,他走过了充满美感的对称的一生。
杂志标题:杨振宁:美即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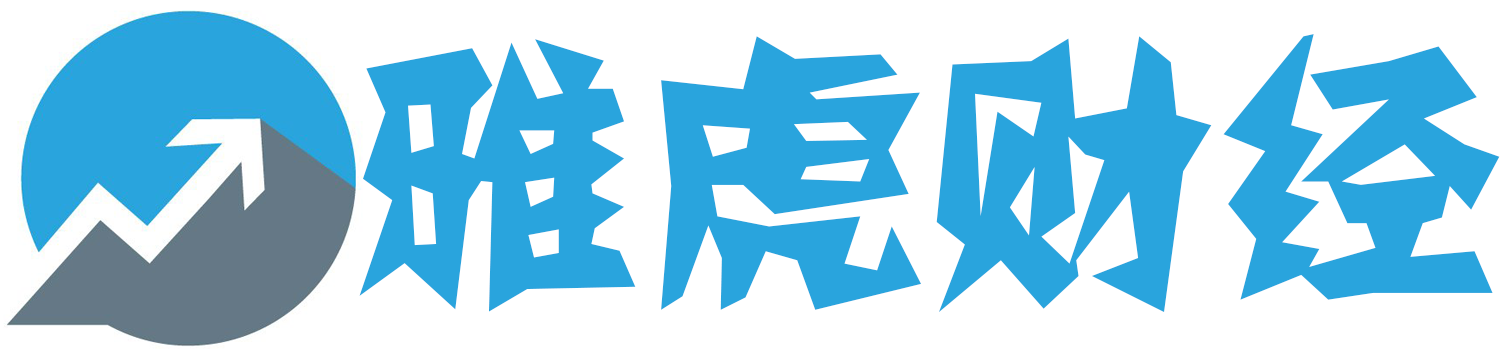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