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咸味幽默的玩笑
刘震云以幽默的方式开了一个咸的玩笑,展现了他独特的幽默感和语言魅力,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文化人物,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这个玩笑的具体内容和背景尚未详述,但无疑为他的形象增添了一抹轻松愉快的色彩。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世间的万千故事中,这大概是最为经典的一则开头了,几乎烙印于所有人的儿时记忆。只是这后面的内容,各自听到的也许并不相同。
如今,以此开头的故事又多了一个版本:“黄河对岸二十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七十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它出自作家刘震云笔下,叙写了一段河南延津的佛门往事,命运流转,禅语迭出,仿若一部当代高僧传。但仅仅万字,述说却猝不及防地再起炉灶,一个名叫杜太白的角色登场,重新引出一干俗人俗事,笔锋斗转地描绘起另一幅喧嚣陆离、悲喜交织的众生相与世情图。
两则全无关系的故事,共同组成了刘震云的长篇新作,取名为《咸的玩笑》。玩笑的是生活,咸的是泪,他在全书结尾的地方写道:“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这个月初,小说付梓,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又说:“笑不经玩,一玩就咸了。”
生活像汪洋大海,文学是取一瓢饮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的新作,名字叫《咸的玩笑》。其实在上一部作品《一日三秋》里,笑话就是贯穿全篇的内容和线索。虽然幽默一直是你的特色和风格,但好像最近的创作尤其将“笑”作为一个表达的核心,就像此前你在《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个阶段似乎有意围绕“说话”这样一个主题反复书写。
刘震云:生活中的笑话还少吗?生活中的玩笑还少吗?但是玩笑跟笑话还不一样,笑话是一个个体的东西,玩笑是个体跟公众之间的关系,笑不经玩,一玩就咸了。
当然,生活底部的东西有时候并不是一个概念能够概括,书名永远是简单的,但是你总得有个书名。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最初的构思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想要写这么一个故事?
刘震云:作为一个作者,总是想下一部作品写得跟以前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在同一个道路上又往前走了一步,而是方向性不一样。一个作者最可怕的就是重复自己,重复几回,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咸的玩笑》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生活中存在一些异彩,这是我之前的作品里还没有涉及过的。异彩是《咸的玩笑》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这种异彩在生活中可能是被掩埋的、被忽略的,但有时候却是一个活法的支撑。
比如书里的裁缝老殷,他特别关注兵马俑,他关注的目的是想看看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活法,又是什么死法。这就是异彩,没有这个异彩,裁缝就是裁缝,但有这个异彩,生活的意义马上就显出来了。
再比如主人公杜太白给孩子起名叫巴黎、纽约、伦敦,他这辈子没去了巴黎、纽约、伦敦,就让巴黎、纽约、伦敦来到他的身边。这也是异彩,是这个人物的支点。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关于巴黎、纽约、伦敦,你以前讲过,这是你老家的一个侄子给孩子起的名字。在《咸的玩笑》里,很多地方都与之类似,比如杜太白小时候外号叫“牛顿”,实际上这是你一个表哥的外号;比如书里一个和尚说1942年的河南灾荒“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实际上这是《温故一九四二》德文版出版时一个奥地利读者说的。因此看上去,这本书整合了你积累很多年的素材,那么它们是先于人物和故事的灵感来源,还是人物或故事已具雏形后才找出这些所谓“异彩”安放其中?
刘震云:两种情况都有。生活中存在这样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未必都适合文学的汲取,生活像汪洋大海,文学是取一瓢饮,具体取哪一瓢要适合这本书,包括跟人物的性格、见识能融到一起。但有时候,生活中的人物未必能达到文学所要求的那种极致的状态,这个时候还需要作家的想象力。
用最质朴的语言说出最深刻的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在结构上也很特别,“正文—题外话—正文”,其实故事的主体是“题外话”,所谓“正文”是题外话。这有点像《我不是潘金莲》,前两章都叫“序言”,最后一章叫“正文”,但篇幅上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序言才是正文。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采用了一种近似于前作的特殊结构?这样的结构设计意欲何为?
刘震云:结构是考验一个作家创造性的最主要的标志,要有自己的思量和胆量。一二三四这么捋下来,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结构,很多人都在用,你要按部就班也没问题,但是文学特别怕按部就班,而且生活的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未必这个因就导致这个果,那个果就出自那个因。
《我不是潘金莲》前边95%都是序言,最后几千字是正文,这在我的其他小说中还没有。小说主要说的确实是李雪莲的故事,但是因为李雪莲,导致了县长史为民下台,所以最后的正文讲的是史为民的故事。
到了《咸的玩笑》,前面的正文写的是智明和尚,中间是讲杜太白的题外话三十三章,后面的正文讲的是泰安的一个小饭馆。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有联系,智明和尚是泰安人、出家在延津,杜太白是延津人,最后离开延津隐姓埋名到了泰安。所以题外是正题,正题是题外,生活中充满这种血脉相连的暗流。
这样的结构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咸的玩笑”,它也许非常有趣味性,趣味性是小说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两个正文里边作者的介入,都是增加这种趣味性,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有意思”是你对创作的一个核心的自我要求?
刘震云:不是核心要求,是第一要求。有意思才能好读、才能抵达意义,这是小说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律。有意思就像大海表面的浪花,有意义是下面的涡流。
《中国新闻周刊》:你追求好读、有趣的那个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语言。我的小说,语言都不艰涩、很质朴,而且句子也比较短、爱用分号。质朴和憨厚是一个自在的状态,没必要把自己打扮得油光水滑。用最质朴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这也是一个文学的境界,浅入浅出、深入深出都好办,但深入浅出非常不好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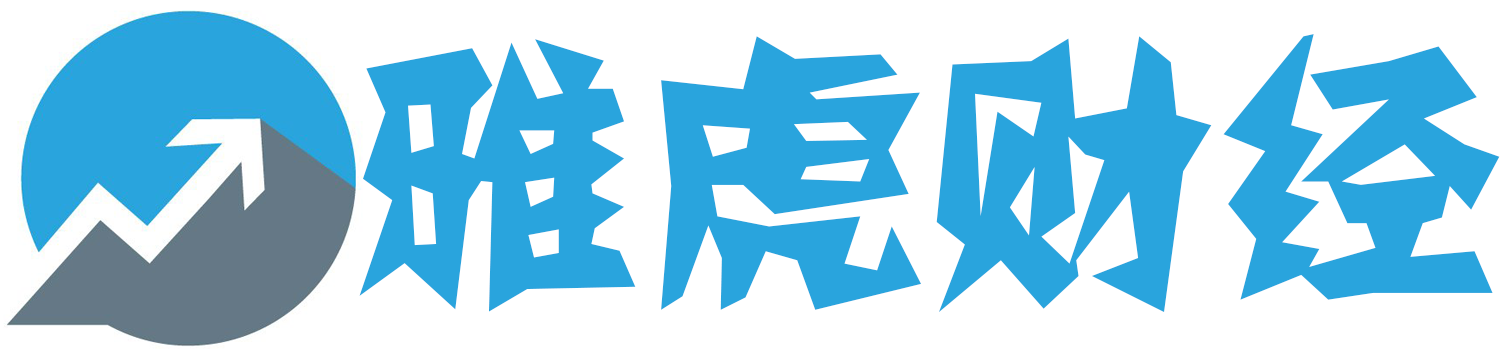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