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化巨头集体大甩卖,行业变革下的挑战与机遇?
日化巨头集体进行大规模甩卖活动,面对市场变化,这些巨头采取积极措施应对,通过降价促销等手段吸引消费者,此次集体甩卖反映了行业竞争加剧和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趋势,也暴露出部分日化企业面临的挑战,摘要字数控制在100-200字左右。
文丨化妆品报邹欣晨
近日,科蒂宣布正考虑出售其大众化妆品部门,其中包括Covergirl和蜜丝佛陀(Max Factor)等知名美妆品牌,一时引发舆论哗然。
实际上,这则备受瞩目的消息仅仅是近期美妆业内一系列关停与剥离事件中的一例:从私募支持的Maesa与好莱坞女星德鲁·巴里摩尔共同孵化的Flower Beauty,再到独立品牌宠儿Ami Colé,这些曾一度在社交平台上“搅动风云”的美妆品牌均难逃“黯然倒闭”的命运。
而除去独立品牌,更多主流美妆企业及欧莱雅、雅诗兰黛等“大名鼎鼎”的美妆巨头也正忙于精简产品组合、重新评判业务规模,通过削减个别品牌乃至于整个业务部门来精简冗余并释放现金流。一些品牌的关停举措震惊了美妆界,像Covergirl这样备受瞩目的品牌也最终登上了被裁撤的名单。然而,随着各大公司优先发展业绩领先的产品线,此类资产剥离与业务关闭浪潮很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01 从并购到出售:巨头们的困境
众所周知,美妆集团往往通过并购行为来发展壮大旗下品牌矩阵,如欧莱雅集团和E.l.f. Beauty等公司就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一家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其中一些运营不善或平平无奇的品牌就难免遭遇剥离或关闭,以便母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在美妆界历来的并购案件中,不乏一些品牌会“鱼跃龙门”攀上大集团成为明星,但更多的品牌则沦为“统计误差”。
譬如欧莱雅集团就选择在2024年剥离植物护肤品牌Sanoflore和Decléor,并在今年将美发品牌Carol's Daughter回售给其创始人,这些举动表明该公司认为其他领域更具发展潜力;科蒂上周宣布剥离彩妆部门,旨在释放资金,以支持其盈利更高的香水部门业务;雅诗兰黛集团也正对其业务进行战略评估,因其连续数季度业绩下滑,而像Smashbox和Glamglow这样表现不佳的品牌正竭力重振市场影响力,以免沦为“弃子”。
“当巨头们在某个品类中取得绝对主导地位后,增长必然趋于渐进,而增长停滞也可能随之而来,二者之间仅一线之隔,这其中的分寸极难把握。”市场咨询公司The Consumer Collective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杰西卡·拉米雷斯指出:“当巨头旗下的品牌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不得不持续创新才能维持其庞大规模。而当创新的速度‘跟不上’市场浪潮时,集团就不得不选择关停部分品牌了——这也有助于集团聚焦核心业务。”
拉米雷斯认为,巨头出现“抛售潮”也侧面反映出,当下消费者在花费自己的可自由支配资金时变得愈发谨慎,他们要求品牌能够不断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此同时,广泛的分销渠道和海外扩张策略已不像过去那样能有效刺激销售增长。此外,各类“咄咄逼人”的独立美妆品牌也对巨头的市场份额“虎视眈眈”,甚至有可能侵蚀后者的市场份额——即便这些品牌最终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它们带给美妆巨头的竞争威胁同样不容小觑。
投资银行Raymond James董事总经理马可·霍瓦特对此评价道:“(科蒂)这些大集团在初期可能占据业内开拓者地位,并保持差异化优势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品牌迎头赶上,同质化产品便会大量涌现,消费者的兴趣也会迅速流失到更新潮、更时髦的独立美妆品牌上了。”
02 渠道压力:零售向下,电商向上
美妆零售格局的重大转变也在动摇成熟品牌的地位。
拉米雷斯观察到,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减少了前往CVS和沃尔格林等线下零售店的频率,转而选择亚马逊等电商平台购物;或因欧美社会的线下防盗措施增加购物摩擦而缩减实体店内消费额,这很可能影响了像Covergirl和Sally Hansen等大众彩妆品牌的业绩。拉米雷斯指出了实体零售对这类品牌相互造成的三重影响:品牌创新速度较慢,零售店自身未能提升店内体验,以及随后因客流量减少而不得不关闭门店。
由于消费者正将更多支出转向在线零售商或沃尔玛这样促销节奏更频繁的大型超市,或者在TikTok Shop和亚马逊上购物。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的美妆巨头可能会发现难以转向并适应像TikTok Shop这样的渠道,而品牌倘若想要“无处不在”(出现在消费者所在的每个渠道),既需要昂贵的营销支持,也需要精准的需求规划。
“你的规模越大,推动公司转型就越困难,”拉米雷斯说。
那些表现优异的品牌,如E.l.f. Beauty和巴黎欧莱雅,已将卓越的数字化能力融入其营销策略,持续投入于通过智能手机触达消费者,用于产品发现和购物。
如今已无万能解药。以往,一个希望加速增长的品牌可能会指望像中国这样的海外市场来提升销售额。但拉米雷斯指出,当前中国美妆市场消费已趋于饱和,企业不得不转向拉丁美洲、中东和印度等规模较小的新兴市场——这些市场虽具潜力,但消费水平远未达到中国市场的同等高度。
同样,进入丝芙兰这样的顶级零售商也不能保证增长,因为品牌需要与海莉·比伯创建的Rhode、蕾哈娜的Fenty Beauty这样由网红和名人支持的社媒大热品牌,以及像Joseon和Aestura这样以亲民价格提供高端产品的新兴韩妆品牌争夺货架空间。
无论一个品牌的知名度有多高,如果它无法规划出一条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那么战略导向的公司就有理由重新审视其在业务组合中的位置。产品与渠道的创新步伐不会放缓。
“残酷的事实是,没有哪家巨头会认为其业务组合中的任何一个品牌是不可撼动的,”霍瓦特说,“人人都可能是‘弃子’。”
0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即便如此,出售一个成熟品牌并不一定意味着母公司的失败,甚至对公司财务状况而言也未必是坏事:此举可以产生更多自由现金流,用于分红、偿还债务或进行更多投资;即使亏本出售,也能带来税务上的好处。
但这表明品牌实现差异化的空间正日益缩小。在如今的美妆市场,“纯净”配方或50余种粉底色号等一度“引人瞩目”的产品特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基本标配,而非“独特卖点”,连跨国巨头旗下品牌都难以维持强势地位。
例如,Covergirl作为美国最早的美妆品牌之一,其超模代言人曾引领时代潮流;Ami Colé曾为黑人及棕色人种消费者带来了专属的奢华理念与高端包装;而联合利华集团在今年五月关闭的Ren Clean Skincare,甚至是最早的“纯净”美妆品牌之一。

随着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拥有成熟商业模式且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的品牌,或许比那些增长迅猛却“昙花一现”的“网红品牌”更受巨头青睐。譬如欧莱雅今夏收购的Medik8与Color Wow两大品牌均拥有逾十年运营历史,其产品系列具备显著差异化优势。“即便出现失误,欧莱雅集团的规模优势亦能提供缓冲——当它在2024年剥离其植物护肤品牌时,旗下仍拥有Cerave等皮肤学级护肤品牌可以吸引消费者。”拉米雷斯指出。
拉米雷斯认为,对于需要季度性提升利润率和增长率的上市公司而言,优化产品组合具有显著财务效益。而维持一个已触及增长天花板的成熟品牌持续运转,无异于资源消耗。
因此,尽管Covergirl和Sally Hansen都是营收达数亿美元的业务(据巴克莱银行估算,科蒂大众化妆品部门整体销售额为16亿美元),但在当前环境下实现规模化增长却更具挑战。尽管“隶属豪门”,但这些美妆品牌面临的考验甚至会比独立品牌更为严厉:若其在品类或地域层面已无明确增长空间,便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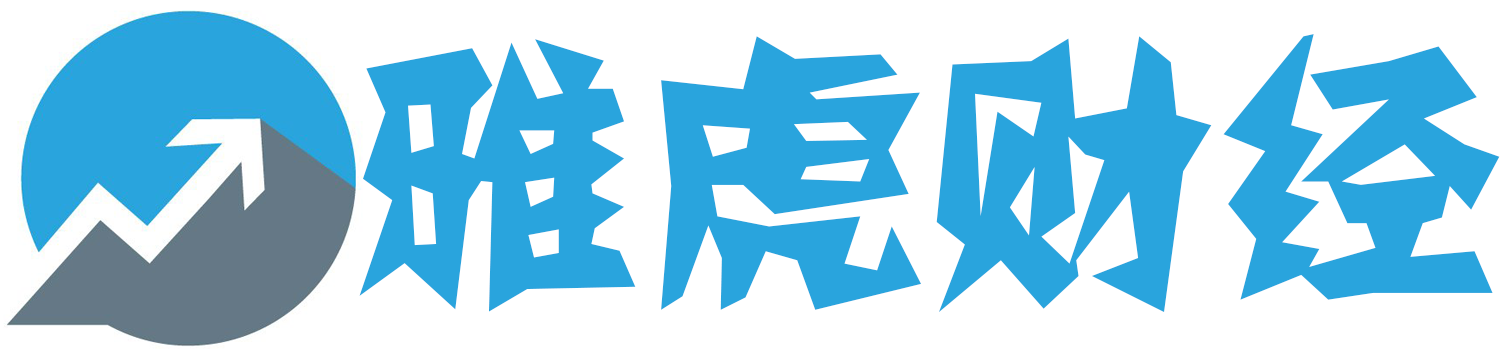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