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谜,能否揭开千年的秘密?
敦煌谜团是否可解,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历经多年研究,仍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探索和理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材料的发现,未来我们或许能够揭开更多谜团的面纱,这段摘要简洁明了,概括了敦煌谜团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
敦煌石窟里有一种特殊气味,那是矿物颜料在挥发,又混合着陈年尘埃的味道。沙武田第一次带着朝圣的心情进入洞窟时,最初的感受就是这种陌生的嗅觉。等到眼睛适应了昏暗的手电筒灯光,彩塑和壁画涌入视线,他一脸茫然,呆若木鸡,事先依靠书本做的功课瞬间失效:“我完全看不懂。”
那是1996年7月的一天,沙武田大学毕业入职敦煌研究院,被领进第246窟。窟内花花绿绿的图像,宛如拼图:“太难了,怎么能把这些都弄清楚?”初入敦煌,一种挫败感围绕着他。
如今沙武田已经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敦煌石窟三十年。他逐渐看懂了敦煌壁画,也有了很多新发现,常常有顿悟时刻。
中国人对敦煌壁画的关注,最早或许起源自一位画家。
20世纪30年代,画家常书鸿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某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他无意中翻开一部《敦煌石窟图录》,编者是法国人伯希和。常书鸿被照片中前所未见的景象震撼。
他回国后多方奔走呼吁,推动国民政府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担任所长,投入毕生心血。身为画家,他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震撼,没忘记吸引他来到敦煌的动因,他一生都在画敦煌。
一代又一代人,从敦煌壁画中看见了什么?
敦煌壁画《鹿王本生图》 图/视觉中国
看见一万五千幅《清明上河图》
相传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来到敦煌鸣沙山东麓,突然见到金光璀璨,好似有千尊佛闪现。受佛光感召,乐僔在断崖上开凿了一个修行的洞窟。不久,另一位法良禅师在旁边也开凿了一个窟。莫高窟第332窟《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上记载了这段故事,唐代人认为,莫高窟开凿始于此,但事迹真假已不可考。
今天能够确认的莫高窟最早的石窟,是毗邻的第268窟、272窟和275窟,开凿于5世纪。在最初的这几个窟里,已经有了壁画。第275窟南壁上,画着一幅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的画。人物上身半裸,下着长裙,有明显的印度风格,但画中城门则完全是中国式城阙。印度等外来元素与中国元素在石窟中并存,这奠定了敦煌艺术的总基调。
一千多年中,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至今,莫高窟保存着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相当于近1.5万幅《清明上河图》的面积。这些艺术品,记录了超过一千年的中国美术史。
敦煌登峰造极的壁画,以第220窟为代表。此窟壁画每幅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南壁《无量寿经变》,气势恢宏,占据整面墙。佛教经变画,是由佛经变成的画作,以供信众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佛教的历史与教义。画中,无量寿佛和三十多位菩萨置身七宝池中,金沙铺地,碧波荡漾,楼阁耸峙,天女散花,呈现出神灵居住的极乐世界。
如同欧洲教堂中那些辉煌的壁画,大多出自无名画师之手,敦煌壁画也是如此。石窟里这些璀璨的壁画,究竟是怎样的高手画成的?从第220窟可窥知一二。
芝加哥大学教授、艺术史学家巫鸿认为,第220窟展现出敦煌从未见过的全新图样。在南、北、东三面墙壁上,描绘着三幅大型经变画,每一幅都是构图精密、内容繁复的佳作,图中人物和细节极为细致生动。
当时,唐朝长安和洛阳兴起一阵美术新浪潮:大量知名画家和高手在寺观创作壁画,留下名噪一时的杰作。这股美术浪潮经丝绸之路影响到了敦煌,敦煌画师依照从中原带来的画稿,在石窟中复刻出中原的流行风尚。
第220窟可能就是以长安和洛阳的庙宇壁画为蓝本而创作。第220窟由翟通开凿,他是“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认为,翟通必定会前往京城参加朝廷考试,及第后授予官职,在长安逗留期间,他完全有可能去寻求新画样,为拟建的家族窟准备崭新的图像资料,从而彰显自身与帝都的文化联系。
然而,由于此窟壁画技法高度娴熟,巫鸿认为,翟通可能直接迎请了京城画师来敦煌,否则很难仅仅按照画稿创造出这种高水平的作品。
而更多的壁画,出自敦煌本地画师。他们留下了璀璨的艺术杰作,却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名字。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无量寿经变》图
看见隐没的历史细节
北宋之后,中原王朝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敦煌日益萧索。直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进入,敦煌石窟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当尘封千年的敦煌壁画再次现世时,令人惊叹之余,首先带来一个困惑:它们画的是什么?只有少数敦煌壁画有榜题,大多数没有文字留存。人们所见,是一面又一面庞大的“极繁主义”、结构多变、富含象征意义的宗教景象,壮观到令人迷茫。
为了“读画”,学者们花费了几十年——经变画表现的是哪部佛经?供养人题记揭示了何种社会结构?丝绸之路如何影响宗教传播?到沙武田初入敦煌时,莫高窟绝大多数壁画内容已被释读,只有少数尚有争议。
“到今天,小画面的释读成果还有很多。比如学界认为的属于西夏王或回鹘王的莫高窟第409、237、148窟王像,我认为应是曹氏归义军最后一任节度使曹贤顺的供养像,等等。”沙武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敦煌壁画还在不断产生新的解读成果。
释读图像最重要的功力,来自对佛教经典的熟稔。以莫高窟第321窟《十轮经变》画的考释,堪称经典案例。第321窟南壁整幅壁画,曾被定名为《宝雨经变》。多年以后,学者王惠民却发现了新的证据。他在南壁找到一方不清晰的三行榜题,根据《十轮经》识读出近30字,与《十轮经》吻合。由此考订出,这是《十轮经变》画,对画面表现的丰富内容也有了新的解释。
直到今天,敦煌壁画中的图像,依然藏着无数解读历史的钥匙。
6年前的某天,沙武田再次走进莫高窟第359窟。他十分熟悉这座洞窟,但就在那天,当他转身凝视东壁门上的供养人画像时,恍然大悟:“这不是粟特人吗?”那个人像他看过很多次了,绿眼睛、大胡子,特征明显。但只有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当他开始关注胡人问题时,才真正“看见”了它。这个发现确认了第359窟是由中亚粟特石姓家族营建的功德窟,也是目前敦煌唯一确凿无误的粟特人营建洞窟。
敦煌壁画常常出现的运输场景中,绿眼睛、大胡子、胖壮的商队首领,明显就是活跃在丝路上的中亚粟特商人。但颠覆常识的一点是,画中作为运输工具的毛驴多于骆驼。沙武田认为,骆驼价格昂贵,大型商队才用得起,中小商队首选的是毛驴。这个小小的发现,修正了人们对丝路的刻板印象。
对壁画内容的考证、释读、定名,属于艺术研究中的“图像学”范畴。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风格学”。两者研究角度的区别,可以粗浅理解为,前者关注壁画的内容,后者关注绘画形式。
敦煌艺术研究史上,图像学与风格学像两条并行又交织的河流,图像学这条河明显更为宽阔和喧腾,这是敦煌壁画研究中参加人数最多、成就最高的领域。然而,当目光落回画面本身,便会发现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风格学”意义上的形式分析,它不追问“画了什么”,而是探究“如何画”。
虽然风格学与图像学是起源自西方美术史的方法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美术,但当人们用风格学的尺子去衡量敦煌壁画,一些文献无法触及的信息浮现了出来。
看见消失的绝世画风
在大唐长安,人们也有逛“美术馆”的习惯。当时的“美术馆”是一些寺庙道观,墙壁上画着著名画家的亲笔作品。其中一位名噪一时的画家,是吴道子,他的主要作品就是寺观壁画。他留下过丹青的寺观,是长安著名景点。
吴道子擅用线条,他将书法的线条用在绘画中,不必依靠色彩和晕染效果,就能营造气势和感染力。据说因为见到吴道子画在寺观的地狱景象,有屠夫鱼贩吓到改行,不敢杀生。这种独特画风以“吴带当风”之名,写在了中国美术史中。遗憾的是,木构的寺观消失在岁月中,吴道子的画也化为乌有。
直到人们打开敦煌石窟,吴道子的神韵似乎在壁画中复活。莫高窟里可以见到不少线描艺术的杰作,出于无名高手。典型的一幅是第103窟东壁的维摩诘像,主体只用线条勾勒,以极为自信的线描勾勒出维摩诘的精神气度。这幅画被认为接近吴道子画风。
中国绘画在初盛唐达到过一次高峰,当时有两种著名画风——吴带当风和曹衣出水。曹衣出水由原籍中亚的画家曹仲达创立,风格源自西域,以墨色晕染出浓淡阴暗,凸显立体感。曹衣出水风格后来影响到佛教塑像,但未见卷轴画流传。吴带当风和曹衣出水一中一外两种画风,在敦煌壁画中相遇,实现了唐代绘画的巅峰对话,并幸运地留存至今。
“当时来看,西来的曹衣出水是正宗的佛教艺术风格,而吴带当风是不正宗的,但他们敢于大胆地不正宗,进行了佛教艺术的本土化改造。”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美术史教研室主任张建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两种典型唐代画风在敦煌的并存,张建宇读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合奏。
敦煌的洞窟里,还上演过更为戏剧性的艺术合奏。
芝加哥大学教授、艺术史学家巫鸿注意过两幅很相似的莫高窟壁画,在第172窟的南北两壁上,如镜像相对。两幅画表现的都是《观无量寿经变》,内容、构图均一致,奇特的是,画风截然不同。
他发现,南壁壁画更为柔和明快,北壁壁画则庄重深沉。前者主色是白和绿,后者色调浓重,反差强烈。凑近看,线条、造型亦有不同。画面中心都是一尊无量寿佛,南壁身躯丰满、双肩斜溜,是盛唐流行的中国化佛像式样;北壁大头、宽肩、细腰,显示出强烈的印度和中亚艺术传统的影响。
似乎可以“破案”了——两幅壁画出自不同画师,代表着不同的绘画系统。巫鸿说,这两幅画是佛教艺术中华夏传统与印度传统的相遇和对照。
不同时期文化因素的并陈与交融,都在敦煌壁画中显形。从十六国到元代,莫高窟营建的近一千年中,每个时代,敦煌艺术与中西方艺术的互动关系都有所不同,是历史沿革折射下的一道侧影。例如,北朝时期,敦煌艺术与洛阳互动密切;初唐至盛唐,敦煌归唐朝管辖,受到长安艺术的深刻影响;中唐时代,敦煌被吐蕃控制,藏地元素进入敦煌;晚唐至北宋的归义军时期,敦煌处于多民族互动之中,包括西域的于阗等地文化风尚都吹拂进来。
中国独步世界的山水画,也在敦煌留下了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沙武田说,中国山水画的革命性变革,在敦煌壁画中清晰可见。南北朝时期,画家对山水的表现还很稚拙呆板,常常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到唐前期,青绿山水画出现,技法成熟;再到宋金时期,出现水墨山水画,演变的历程被记录在敦煌壁画中。尤其是年代可信的传世唐代青绿山水卷轴画难得一见,而敦煌则清晰可见。
位于莫高窟第172窟北壁(上图)和南壁(下图)的《观无量寿经变》图
看见中国古建的隐秘档案
1930年,时年29岁的建筑学者梁思成,进入新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最初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写成了一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这是研究唐代建筑的拓荒之作。然而,当时中国尚未发现任何一座唐代佛寺和宫殿,文章如何下笔?
梁思成的资料来源之一,是文献中关于唐代建筑的记录,而更重要的素材,就是常书鸿也见过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一组“凹”字形建筑群,三面相连的多层楼阁,围出一片广场,佛居于广场中间。佛身后的中央大殿,由前殿、中部阁楼、后殿衔接而成,三重起伏错落,繁复而庄严。中央大殿通过连廊与角楼连接,角楼又通过连廊与两侧配殿相连。这是敦煌初唐第172窟经变画中细致刻画的佛国盛景。
“人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组建筑主殿与配殿,高起的殿堂与平缓的走廊,高低错落,起伏有秩,具有鲜明的节奏感,仿佛是一段优美的乐章。”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美术史学者赵声良高度赞赏这组建筑的美感。整组建筑沉稳而宏大,屋顶平缓,殿堂宽阔,斗拱谨严,体现着气度雍容又自然淳朴的本色之美,“是唐代宫殿建筑的写照”。
对于这组建筑的身份,巫鸿有过更具体的推测:原型很可能来自皇宫建筑。634年,唐太宗建大明宫,三个主体建筑——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都以主殿和两翼构成,与壁画描绘的佛国天堂如出一辙。
梁思成对壁画中唐代建筑的判断,很快便幸运地获得了现实印证。1932年,写完这篇文章不久,梁思成前往蓟县考察独乐寺,一眼看出其与敦煌壁画中的唐构十分相似,并准确地将其断代为辽代建筑。辽承唐风,一脉相承。
莫高窟第61窟壁画的《五台山图》,尤其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第61窟开凿于唐朝之后的五代,敦煌画师对五台山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绘。五台山是唐朝第一大道场,壁画中标注了五台山主要佛寺的位置,其中有一座“大佛光之寺”。
莫高窟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局部中的“大佛光之寺”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前往山西五台山,在崇山之中找到了佛光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发现的第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唐代木构建筑,被视为“无上国宝”。他们此行便是以敦煌《五台山图》为路线图,这幅敦煌壁画,千年之后竟然仍是一张有用的地图。
后来,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唐代一章的主要资料,依然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将唐代的建筑——宫殿、佛寺,乃至平民住宅——在佛像背景里一概忠实描绘下来,使得未发现当时的木质建筑遗物的我们,竟然可以对当时建筑大概情形,仍得一览无遗。”梁思成感叹,“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
5月28日,人们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摄影/本刊记者 盛佳鹏
看见敦煌壁画生生不息
敦煌壁画在石窟里沉寂了上千年,国人领略到敦煌壁画的魅力,不过至今百年来的事。其中关键事件之一,是1939年8月在西安举办的“敦煌石窟艺术展”。展览上的明星,是一幅高2米、长15米的巨幅长卷——《极乐世界图》。
这幅长卷原型出自敦煌莫高窟,将它“搬出”洞窟、面见世人的功臣,是画家李丁陇。前一年冬天,李丁陇辗转抵达敦煌,在一个阴冷的洞窟里安顿下来,每日披一床破被子,辗转于各个洞窟临摹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展”在西安引发轰动后,又在成都和重庆举办,引发了张大千的兴趣。张大千1941年率领队伍来到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系统踏勘,临摹了近千幅壁画,还为洞窟编号。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弘扬功不可没,但由于对部分壁画进行了人工剥离,而且临摹壁画时往往直接贴在壁画表面,对壁画造成破坏,引发学者和社会舆论的质疑,张大千不得不在1943年离开敦煌。
在敦煌保护历程中,一大批画家对敦煌壁画起到了重要的临摹、弘扬、保护作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前两任所长常书鸿和段文杰,均是知名画家。谢稚柳、王子云、关山月、董希文、常沙娜等艺术家,都曾临摹敦煌壁画。常沙娜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弘扬,经过她的设计,人民大会堂等建筑中使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元素。
张建宇说,从敦煌临摹的壁画,本身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材料,而经由敦煌艺术所衍生、启发的艺术,至今生生不息。这两年,他就看到了多场敦煌主题的当代艺术展览,今年由巫鸿担任学术主持的《登临出世界》,展出了当代艺术家根据敦煌艺术创作的作品。
百年来,敦煌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从历史到地理,从艺术到宗教,从建筑到文物……对敦煌石窟的解读至今不绝。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敦煌是避不开的课题。
张建宇认为,如今,敦煌艺术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其次是美国,日本和欧洲逐渐式微。美国的敦煌研究,以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方闻和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两位艺术史家为中心,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批学者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
张建宇就是其中一位。他2007年跟随方闻攻读博士学位,参与“汉唐奇迹在敦煌”课题研究。张建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在二维的画面上,中国人如何表现三维世界。听起来简单,却是理解中国绘画发展的关键线索。敦煌壁画成为他观察中国艺术空间观念演变的极佳标本。他以敦煌为箭矢,指向整个中国美术史。
“从北朝的稚拙到隋唐的成熟,在敦煌壁画中,能清晰地看到画师们如何一步步解决空间表现这个核心难题。”张建宇说。比如,第217窟、103窟、172窟等窟内青绿山水的空间营造,与同时代长安画家的创造遥相呼应。虽然敦煌画师未必比得上长安的名家,但他们敏锐捕捉到了最前沿的艺术风尚。
敦煌壁画反映的不仅是某个时代的艺术创作,还是半部流动的中国艺术史。“敦煌提供了中国绘画史中最系统、最完备、最连续的一批材料。“张建宇说,虽然也可以从墓葬壁画中拼凑出那些时代的艺术面貌,但没有任何地方能像敦煌这样,提供如此完整的视觉证据链。
“我常对学生说,做敦煌研究不愁找不到题目,”沙武田说,“只要你走进洞窟,一定会看见新东西,正所谓常看常新。”他刚刚出的一本书,是通过敦煌壁画看更加真实具象的丝绸之路,他看见了壁画中那些骆驼、毛驴、大象、联珠纹,看见了胡商、罽(jì)宾人、新罗人、外道女性和行脚僧,也看见了更生动、高清的历史现场。
杂志标题:解码敦煌壁画:凝固的千年美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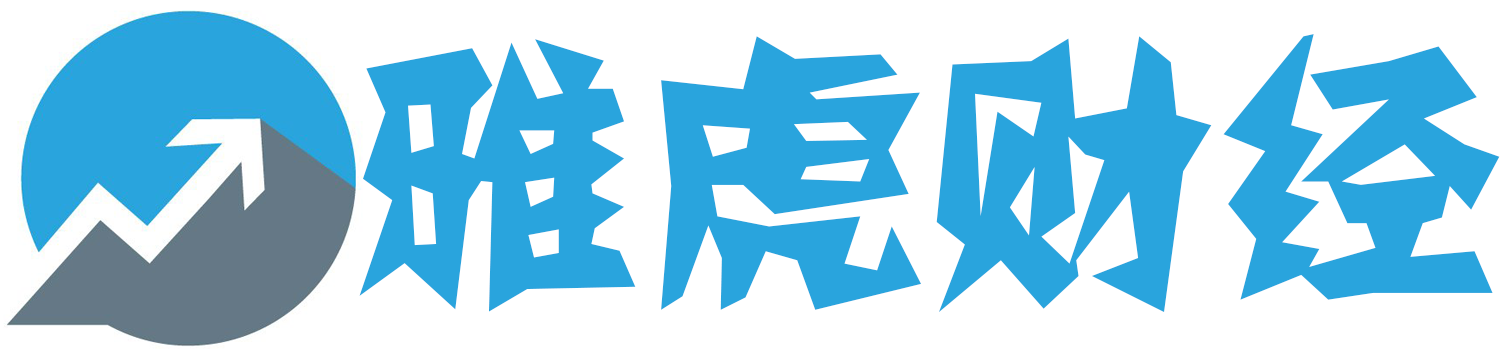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