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沉默的荣耀
本文展现了真正的“沉默的荣耀”,通过描述那些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人们,他们虽不张扬却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带来正能量,这些无声的英雄,虽没有璀璨的光环,却在平凡岗位上展现了非凡的品格和力量,他们的存在,传递着温暖与希望,成为社会的骄傲。
国新社“001号”职员证,被老记者陆诒小心地保存了一辈子。这是国新社1938年创办时,由时任社长范长江用毛笔手书的。
近日,周恩来侄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与范长江、金仲华、陆诒等国新社创始人后代齐聚桂林,出席了“国新社在桂林——抗战时期国际新闻传播研讨会”。会上,陆诒之子陆良年将家藏的多件史料捐赠给了中新社。
国新社,即国际新闻社,是如今两大国家通讯社之一中国新闻社的前身。抗战时期,国新社打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国内舆论,进而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途的民意。
然而,国新社本身却隐没在这一巨大影响力中,当时就鲜为人知,后来更湮没不闻。很多人饱经坎坷,一些人失去生命,成为另一种“沉默的荣耀”。
范长江、陆诒等国新社部分人员在桂林留影。本文历史资料图/ 《范长江在桂林——抗战时期红色新闻资料专辑》
生于乱世
国新社的诞生,就跟1938年的抗战形势一样,用“艰难困苦”不足以形容。
这年9月30日,范长江代表筹备中的国际新闻社,与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国际宣传处签订了供稿协议。协议规定,国新社负责提供“有利于抗战建国及暴露敌方弱点”的国际宣传材料,国际宣传处每月支付若干固定稿酬。在内容不重合的前提下,国新社可向国内及华侨报刊供稿。
但国新社还没来得及成立,武汉沦陷了;撤退到长沙,长沙大火了。11月21日,国新社终于在桂林安顿下来,正式开张。
初到桂林,还在旅馆打地铺时,范长江就派出三路人马,奔赴战地采访。陆诒带着任重、高咏和叶厥孙三个青年记者赴广东战区,高天、石燕和彭世桢在广西采访,于友入湘鄂赣。三路人马一边采访,一边发回战地通讯。
撤退到重庆的国际宣传处于12月1日开始办公,第二天,国新社的首批稿子就到了。处长曾虚白很高兴,给范长江写信说:“可称是我们各方努力配合妥切的表现,深足庆幸。”
桂林时为广西省省会,居民从战前的五六万猛增到几十万,到处都客满,他们好不容易才在环湖北路19号一座院子中转租到几间房子,作为社址。从咯吱咯吱响的木梯上去,是一间直不起腰的阁楼,这就是集体宿舍。用范长江的话,一间如沙丁鱼一样地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地办公。
环湖北路19号,也是“青记”的会址。青记全称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是一个中共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范长江、陈同生(当时叫陈农菲)等是其负责人,当时会员已发展到600多人,遍及全国。国新社与青记可以说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组织:青记为国新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国新社为青记提供了发稿平台。
1939年初,陆诒这一队结束了在广东战区的采访,溯西江而上,从梧州进入广西。桂系在广西推行政治上自治、经济上自给和军事上自卫的“三自政策”,全省皆兵,有“模范省”之称。因此他们一进入广西,就感到一种强烈的抗战氛围,各处井然有序。
1月7日,陆诒在桂林访问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当时桂系三巨头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抗战前线指挥作战,黄旭初在广西当家。
陆诒回忆,黄旭初身材矮小,平头,年约四十岁,穿一套广西公务人员常穿的灰布制服,态度谦恭有礼,回答问题却特别谨慎,莫测高深。他要陆诒谈谈对桂林的观感,又问他广东战区的情况,陆诒向他提问,他就打太极,重复自己的口头禅“倒是、倒是”。
这次,“倒是先生”遇到了有“然而先生”之称的陆诒。陆诒有备而来,在他的“倒是”之间突然问起广西出征抗战部队的数字和每年的“壮丁”数字,使得他不得不做了一个还算直接的回答。
黄旭初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桂系与蒋介石历来矛盾很深,抗战时期虽以合作为主,但无疑也有自己的算盘。周恩来安排范长江等落脚桂林而不是重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在桂系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下,桂林迅速崛起为大后方的文化名城。在几经颠沛之后,国新社终于有一个适于发展之地了。
2025年10月,陆诒之子陆良年、范长江之子范小军、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和金仲华之孙金进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的国新社展览前合影。摄影/蒋雪林
“设计师”
没多久,被称为“文化界的参谋长”的胡愈之也来到了桂林。胡愈之在国新社没有正式职务,只担任常务理事。但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国新社事业的“设计师”和“灵魂”。
抗战前,胡愈之就活跃在上海出版界。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也是《世界知识》和《生活》周刊等多家知名刊物的创办人或策划者,还曾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即法新社前身)上海分社任编辑主任。邹韬奋说他对出版事业“无所不精”,“计划力极为朋友们心折”,绰号“诸葛亮”。胡愈之还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就是“功成不居”,总是成人之美。
国新社的成立,胡愈之可谓是幕后的推手。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了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正是胡愈之。他们除编写材料向外国记者散发,还办了一个小型通讯社,取名“国际新闻供应社”,向华侨中文报刊发稿。上海沦陷以后,经胡愈之的安排,王纪元、郑森禹等撤到香港,成立独立的通讯社,定名为“国际新闻社”,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武汉会战后期,曾虚白任处长的国际宣传处与范长江联系,希望聘请他担任战地通讯员。胡愈之当时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文字宣传,与新闻界联系很多,范长江与他也有私交,就找他商量。胡愈之出了一个主意,经请示周恩来,决定由范长江这样去跟曾虚白交涉:“我一个人去没有用,要去我们就成立一个国际新闻社,用一批人,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供应。”曾虚白同意了,而且还同意列名,因此他的名字被赫然列在国新社创始人名单之首。
抗战时期的范长江
1939年2月,胡愈之赴香港,办理了桂林和香港两社的合并事宜。两个通讯社同名,这并非巧合,而正是他埋下的伏笔。
香港国新社设在九龙弥敦道49号,青记香港分会也设在这里。专职人员只有王纪元、恽逸群、刘思慕、郑森禹等少数几人,但《星岛日报》的金仲华、邵宗汉、羊枣等和《世界知识》的张明养等都是国新社社友,共同参加类似社务委员会的“叙会”。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香港新闻文化界的餐叙、聚谈圈子,斯诺、爱泼斯坦等有时也参加。
合并后,桂林为国新社总社,香港为分社。双方互换稿子,都如虎添翼。
国新社的产品线,简而言之就是两条:一是通讯,二是专论。
所谓通讯,是相对于电讯稿而言,经邮局寄出,不受字数限制,因而逐渐演变成一种文体。青记会员就是国新社天然的通讯员队伍,国新社的战地记者出去采访也都带着任务,在“能动笔杆子的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通讯员。这些来自一线的鲜活通讯由桂林寄到香港后,香港分社再转寄海外华侨报刊,一时间订户大增。
专论类似时评,国新社的评论作者名家如云,特别是国际时事评论,几乎是独此一家。九一八事变以来,很多人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自身命运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国际评论成为热门。胡愈之创办的《世界知识》就是其中翘楚,他所撰写的发刊词“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传诵一时。在香港的《世界知识》作者现悉数成为国新社的作者,阵容是碾压式的。
胡愈之为国新社设计了一种分区发稿的独特发行模式,称为“特稿”,即一篇特稿在一个地区(如西南)只供应一家报社。抗战时期交通隔绝,这形同独家特稿。发稿时一般用复写纸复写六份,一份邮寄香港分社,另外五份分寄各地区。
订阅国新社稿件有三种选项:甲种为每月供稿30篇,乙种为每月20篇,丙种为10篇,收费不等,采用与否自便。发表时由作者具名,不用国新社名义。胡愈之认为,“人怕出名猪怕壮”,过于抛头露面是自找麻烦。而且,不用国新社名义,报纸用稿时可以黑体字标上“本报专稿”“本报特约专稿”,对订户也更有吸引力。
9月,胡愈之又设计了一种新的业务:出版油印的《国际新闻通讯》。《国际新闻通讯》每周一期,材料来源是香港分社通过航空寄来的外文报纸,由人称“铁公”的张铁生和彭世桢编译。报馆和私人皆可订阅,报馆订户为航寄10元,快寄8元;私人订户为航寄8元,快寄6元。
这项业务对油印等技术要求很高,社内会写文章的多,懂刻蜡纸的少。朱海民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来社后立刻承担起缮抄、油印、装订、寄发的全部工作。经他手发出的刊物字迹清晰端正,发寄及时,广受欢迎。
环湖北路21号
大约在1939年春,国新社告别了“叠罗汉”式办公,搬了新家。青记则留守原处。
新址在环湖北路21号。这是一栋新建砖房,国新社在二楼,占据了五间房。专职人员发展到20来人,设编辑部、采访部和经理部。
社长范长江,兼采访部主任。他常穿一身草绿色哔叽开领上衣,同色马裤,皮靴闪亮,一副战地记者的英姿。他那时刚30岁,却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目光炯炯,是全国进步新闻界的核心人物。
编辑主任(相当于总编辑)黄药眠,留一把大胡子,从范长江起,大家都叫他“黄大师”。社友王淮冰回忆,文人相轻是存在的,在国新社也一样,但对黄药眠大家都由衷地钦佩。他对稿子很严格,该退的退,该改的改,“像一个高明的医生”。
黄药眠文人本色,有时会感到劲头不足。范长江总是给他打气:“你要沉得住气,我们今天是稿子的发行,将来是人的‘发行’。”范长江爱才如命,有时手捧着青年人的投稿跑来对黄药眠说:“请你看看,这是多么好的报道!文章写得多漂亮!是一个人才、人才!”
每周或隔一周,范长江、胡愈之和黄药眠要开一次社务会议,由秘书唐勋记录。
经理孟秋江是范长江的老搭档,他被范长江从《新华日报》要来,离开记者本行,担任国新社大总管,天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他经常穿一身干净挺括的中山装,提着社里唯一的公文包,带着一脸“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的神气,迈着轻快的步子出门。但王淮冰却多次看到,他悄悄来找范长江。范长江通常在找人谈话,见他紧锁双眉、欲言又止地进来,就微笑着看他,意思是“不必多说,还是你去想办法吧”,孟秋江只好摊摊双手,转身出去,继续奔走。
国新社实行“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没有投资方,会员以稿费入股。领导层由社员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产生。专职人员不拿工资,从范长江起,每人每月只发15元零用钱,只有黄药眠另有20元津贴。而在战前,胡愈之在哈瓦斯通讯社的月薪高达320元。
在这里,大家是一种救亡团体式的集体组织,生活清苦,吃饭守着一大脸盆的大锅菜,找一片肉像“开矿”。但这种生活方式对流亡文艺青年另有一种吸引力,同事之间一律平等,讨论业务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桂林独特的山水之美,也为他们的生活平添了诗意。他们爱在周末带着干粮去郊游,或者在微雨中在榕湖边的树林里散步。
谷斯范曾回忆,夏天他们经常去漓江游泳,租一条船,荡漾于象鼻山前。江水清澈,江底是软沙,水不深不浅,是再理想不过的天然泳池。有人划船叫卖芝麻糊,胡愈之请客,每人一碗芝麻糊。“天上蓝天白云,远处奇山异峰,坐在船上喝着甜甜的芝麻糊,观赏这绝世风光,此情此景,仿佛还在目前。”
11月21日是桂林总社开张一周年纪念日,国新社举行了招待各界的年会。
这时的国新社,已成立了重庆办事处,设立了金华办事处和洛阳通讯站,还在沦陷区的上海秘密派驻了特派记者。社友从初创时的13人发展到60多人,通讯员两三百人,订稿用户达到150家以上,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庆典前夕,宽大的会客厅洗刷一新。墙上的《自由壁报》以“1940年的展望”为总题,贴着许多短文。胡愈之、范长江和香港分社负责人王纪元写的《我们的计划》谈到,经费要增加到多少万元、通讯员要遍及全国,还有社友写道,“我们要跟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竞争”。
国新社、青记与生活书店部分女工作人员在桂林合影。
黑云压城
然而也就在此时,国共摩擦的阴云正渐渐聚集,风雨欲来。
1939年4月,国民党中央秘密印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这年下半年起,国际宣传处就没有再订国新社的稿子了。
1940年,对国新社的限制进一步收紧。这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国际宣传处发去了一份公函。公函称,据桂林方面密报,国新社“气魄颇大,事业亦日趋发展,其所编发之各种稿,甚能适合一般报纸之需要”,因此要“特别注意审查”。
7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向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监察局发去一份“快邮代电”(即以快邮方式寄发的密电)。密电称,范长江“活动力甚强”,思想“已渐左倾”,其主持下之国新社“规模甚大”,“发展甚速”,仅以通讯员一项已达260人之多,“尤以左倾分子义务工作者居多数”。电文中特别提到,该社所出的《国际新闻通讯》月出四期,“其材料均系报端所禁载者,故极为珍贵”。
这份密电还称,已密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对国新社的金华通讯站等分社和通讯站严加取缔,并要求桂林新闻检查所对该社稿件“严密审查”。
国新社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头换面,但还是订户日少。一些报社也不能及时结清稿费,经济来源日蹙。
1940年春末,为了节省房租,也由于常要躲避敌机轰炸,国新社在近郊找了一处茅舍,隔成大小数间。每人床前一张办公桌,晚上点煤油灯。
气氛日益紧张。大门口坐着一个永远不补鞋的修鞋匠,矮墙外有人探头探脑,收到的信件和稿子常有被拆阅的痕迹。不时有传言说,当局有个黑名单,随时可能来抓人。
这年春,秘密潜入北方沦陷区采访的记者李洪在归途中,行至皖北地区后突然失联。直到一年多后,才得知确切消息。原来,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抓住后在夜里活埋。
1940年秋,李克农递给胡愈之一张机票,让他第二天就走。他提了一只箱子,只说家里有事要回去看看,悄然飞去香港,再转至新加坡。
在香港期间,胡愈之去见了陈翰笙,请他为国新社编写英文通讯稿。陈翰笙此前在美国编《华侨日报》,与美国新闻界以及影响很大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联系密切。
此后,陈翰笙开始为国新社编半月刊《远东通讯》 (Far Eastern Bulletin),道林纸油印,用航邮寄发。订户达300多,包括海外报刊和通讯社,也包括一些机构和个人,如美国国务院、美国记者斯诺和爱泼斯坦等都是订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远东通讯》第一时间报道,成为第一家向海外介绍皖南事变真相的英文媒体。在国外的朋友告诉陈翰笙,这“揭了国民党政府的底”。
多年后,曾虚白在回忆录中不无怨恨地把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左翼记者称为“流浪记者”,说他们一面倒地变成了中共的代言人。抗战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董显光也感叹,抗战过程中英美报刊“泛滥着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标榜他们八路军战绩”的宣传文字,“后来扩展而影响全美民意”。
皖南事变期间,恰逢国新社第二届年会在桂林举行。一时间,有如黑云压城。
范长江从重庆办事处回到桂林总社,主持了年会,做了“国新两年”的报告。
他感慨,新闻事业是政治上最尖锐的事业。两年来,国新社同仁始终不动摇,不悲观,不浮动,沉着应战,今后也将继续努力前行。
在这波反共高潮中,桂系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态度。黄旭初等还奉送机票,“好来好往、暗中送走”。
1月底,范长江戴一顶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离开桂林,飞往香港。国新社其他工作人员也陆续疏散,一部分去延安等根据地,一部分去了香港等地。
黄药眠回忆,离开的时候春雨连绵。桂林山水笼罩在烟雨朦胧中,一条条雨丝割裂着黄昏,让人思绪万千。
上图:国新社1939年编印的社员名册录(部分)。 下图:1940年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 图/陆诒藏
“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
这年4月28日,国新社总部和青记总会在同一天被国民党当局关闭了。
重庆办事处也随即结束工作。离开猫儿石前,办事处工作人员高天把国新社和青记的文件、信件、材料,社员、通讯员的通信地址付之一炬。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分社也被迫关闭。
抗战胜利后,国新社上海办事处于1946年12月建立,由孟秋江主持,但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上海办事处坚持了近两年,全面内战开始后被迫停止活动。
国新社香港分社于1946年年初重建,从九龙弥敦道49号迁到了香港半山区坚道20号。10月,陆诒奉命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主持国新社工作。这期间,英文《远东通讯》也恢复了。
1949年春,香港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香港分社社友刘尊棋、孟秋江、高天等先后离港。留港社员写信给胡愈之、范长江等理事,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不久他们复电称,国新社历史任务现已基本完成,不必再做单独发展计划,凡愿赴解放区工作的即可离港。5月,陆诒离港回到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央筹备成立一个以对外报道为主要业务的新闻通讯社。最初的设想是“扩充并加强国新社”,考虑到与当时美国的国际新闻社同名,最后定名为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
首届中新社理事会由33名理事组成,其中13人为原国新社成员,他们是:金仲华、邵宗汉、郑森禹、王纪元、胡愈之、刘思慕、陈翰笙、刘尊棋、陆诒、萨空了、孟秋江、高天、黄药眠。范长江参与了中新社筹备工作,但没有参加理事会。
当年10月1日,中新社正式成立,对外发稿。金仲华出任社长,王纪元担任副社长。国新社名称停止使用,其用户转为中新社用户。
国新社的人和事逐渐淡出,以至于沉寂。由于当年所经历的复杂斗争,很多国新社人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饱经坎坷,或被错划右派,或被迫害致死。
改革开放后,胡愈之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怀着很深的感情,写了多篇纪念文章。
他写道,1939年的桂林环湖路,“其时,其地,其人,是我再也忘不了的”。国新社是在周恩来亲自筹划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成为党在解放区以外的新闻战斗堡垒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范长江等都已沉冤昭雪,国新社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1981年4月25日,40多位国新社老人在北京饭店东二楼重聚。85岁的胡愈之和大家握手、合影,都激动不已。
社友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于1987年结集出版了《国际新闻社回忆》。社友夏衍为该书作序,他写道:“到现在,即使在新闻界,知道‘青记’和‘国新社’的人,可能也已经不多了,但是,范长江、孟秋江、金仲华、陈同生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
多年来,随着一个个老人的离世,国新社越来越远去。无论是哪一轮历史热,它都无法赶上。因为永远无法确知,到底有哪些稿子是国新社发出的,也就无从搜集和研究。隐于上千篇稿子之后的国新社,或许注定只能如冰山静默在水面之下了。只有冰山一角,偶尔被人看见。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其中之一。
2001年,英文写作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在黄仁宇去世一年后翻译出版。书中他写道,范长江“倾其所有”创立了国新社,“事实上就是卖特稿的通讯社”,在重庆、桂林和香港设了办公室,就像连锁公社一样。幸运的是,在“联合阵线”期间,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处支持它。即便如此,国新社的日子仍然过得艰苦无比。“月复一月,他们卷铺盖席地而睡,餐餐无肉成为常态,每个月的津贴只够剪头发和买邮票写信给亲友。”
之所以如此关注国新社以至生活细节,或许因为,黄仁宇差一点就成为一位国新社社友。
时间回到1938年7月。20岁的他作为《抗战日报》一名崭露头角的记者,参加了青记长沙分会,并负责整理名单。那年夏天,他去武汉投考黄埔军校,其间常待在青记总会,帮着范长江和陈同生等跑腿打杂。他被录取后,要退出长沙分会的工作。那时范长江正在长沙筹办国新社,竭力想说服他放弃从军,留下来继续干。不用说,没有成功。
在黄仁宇印象中,范长江很容易激动,还有些天真,赞成时习惯一拍桌子说:“好,就这么办吧!”无论对方是提议出去吃一碗面还是油印一份传单。在范长江眼里,似乎一切都有必然联系,不管是他自己还是黄仁宇,都必须“肩负人类的命运”。陈同生则总是微笑着,对一切艰难困苦毫无怨言,是那种共产党内无名英雄的典型。在黄仁宇看来,他们都是给予者,而不是接受者,非他自己所能及。
他写道,时隔多年,对范长江等人的回忆让他重新检视自己,有时还会产生自我怀疑,最后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或许,被影响的还有他的整个大历史观。
(本文参考了《国际新闻社回忆》《范长江与青记》《范长江在桂林》、靖鸣主编《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方蒙《范长江传》、于友《胡愈之传》、陆诒《文史杂忆》以及孟秋江、陈翰笙、黄仁宇等的回忆录和文集)
杂志标题:国新社的桂林往事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cbern.net.cn/post/4811.html发布于 2025-11-17 15:01:00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雅虎财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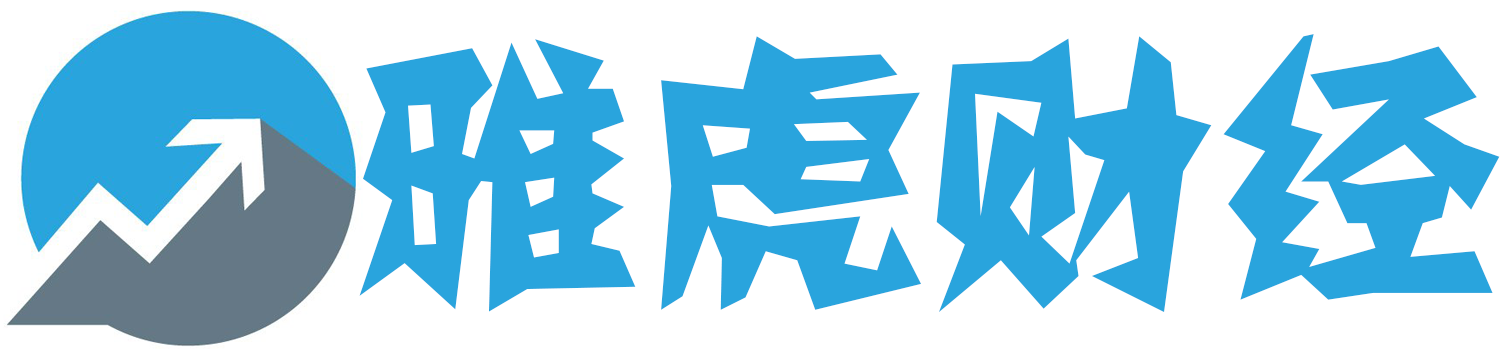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