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偶像易烊千玺与李健,他们的共同追求
该人物深受易烊千玺和李健等人的喜爱和支持,拥有众多粉丝,关于他的更多信息尚未透露。
三十年前,沈阳铁西区有一位老人,老人住在旧式住宅楼的底楼,光线阴暗,屋子逼仄,但装满旧书。那些书收藏自久远的年代,品类庞杂,有不少通俗读物甚至地摊读物混杂其间,但装着一个老人对书的热爱。后来,老人去世,书也不知所终,那个热爱读书的老人,彻底消失在时间中,没留下任何物证。
但班宇记得他。那个人是班宇的太爷,算起来,比他高三辈。太爷喜欢班宇,每次班宇来玩儿,他就背起一个箩筐,去给小孩买好吃的。班宇记事时,他已是耄耋老人,两人交情不过几年,但他始终留在班宇的记忆中,包括那些书,那间清凉的小屋。多年以后,班宇写起了小说,他把太爷的形象连同那间小屋都编进了故事,在文字里为童年回忆重新上色。
这是班宇中篇小说《白象》的部分灵感来源。同名小说集最近出版,是他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的第四本中短篇小说集。作为最受期待的青年作家之一,班宇的小说宇宙从东北出发,大雪覆盖的东北平原上,他的故事里寒风吹彻,《冬泳》《肃杀》这样的标题就令人寒意顿生。
写作《缓步》的时期,班宇试图抽离出东北,跟自己较把劲,摆脱掉标签。而在《白象》这部新小说集中,他不再纠结于此,又回到东北。只是故事不只发生在沈阳,还拓展到长春、佳木斯等地,“统摄了一下东北”。
“这五篇其实在讲一个事,就是一个人的现在,是怎么被过去改变的。这是我这两年想得比较多的事,一篇小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班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年影视和文学界兴起的“东北文艺”,常常以残酷凶案为典型载体,但班宇的笔下少见奇观与奇案,寒意是从人生里慢慢渗透显形的。在没有恶人的日常中,重如玄铁的是生活,冷若冰河的是时间。这是东北,也是世界。
记忆
长大以后,班宇才慢慢知道一些太爷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正暗合几十年的当代史。幼年擅长读书的太爷,因为时代变迁失去读书机会,后半生在运动中浮沉,终究未再受过多少教育,阅读热情也终究无力兑现成某种形式的输出。祖辈故事促使班宇开掘小说的历史纵深,从之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叙事,向20世纪中期乃至前半叶掘进。
太爷那间水磨石地面的清凉房间,化身成为《白象》中的场景。故事中另一个重要布景,是防空洞,在东北,防空洞就像旧年月的飞地,承载着一段曾经装满恐惧与不安的生活。到了班宇小时候,封锁已久的洞穴早已成为遗址,装满孩子的好奇。小孩们经常大声敲击洞门,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东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班宇小时候,不同年代建造的城市空间并存,几个时代的记忆层层堆积。班宇提笔写小说,也是为了给一些沉重的记忆寻找出口。
大学毕业后,班宇一边在一家古籍出版社上班,一边在网上写乐评。他对摇滚乐的热爱始于12岁那年,渐渐地,“坦克手贝吉塔”这个笔名在乐评界颇有名气。快到30岁时,音乐杂志陆续停刊,他也感觉以评论抒怀,是借他人作品浇心中块垒,总是隔着一层,于是动笔写小说。2016年,他在豆瓣征文比赛中写了一组以沈阳铁西区工人村为题材的故事,用东北语言的幽默化解命运的沉重,获得了喜剧组第一名。
工人村的故事打开了班宇的记忆阀门。那是被“下岗”魔咒支配的世纪末,一股沮丧的气息弥漫在家里和社会上。他的父母在沈阳变压器厂工作,厂子巅峰时有十万职工,中学时,他的母亲被卷入下岗潮中。有次家庭聚餐,大家猛然发现,满座亲戚中,除了班宇父亲,其他人都离开了工厂。生于1986年的班宇,在这种沉闷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记得有一个要好的同学,从父亲下岗那天起,好像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那场变局造成的伤一直隐隐作痛,“遗传”给了“80后”一代,最终由他们来讲述。后来,班宇说,记忆就是敌人。他不断讲述父辈经历的事,就是为了搞清楚,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理解才能和解。
“就像《白象》里的李小天,如果他不把这事(往事真相)解决了,也活不下去,因为几代人全遮蔽在这个阴影里。他必须得给自己一个或真或假的解释,才能继续向前看。”班宇说。
凭借对东北题材的优秀发挥,班宇迅速成名,2019年,他出版于前一年的首部小说集《冬泳》,因为易烊千玺和李健的阅读、推荐,进入更广阔的读者视野。而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内部,2018年秋天在《收获》发表的《逍遥游》更为重要,曾托举过先锋作家的评论家李陀,难掩激动地为这篇小说撰写长篇评论,盛赞不已。在知名作家们参与的《我在岛屿读书》节目中,《收获》主编程永新向余华、苏童等作家谈起这篇小说,说编辑几乎一字未改。《逍遥游》彻底展示了一个一出生就羽翼丰满的年轻作家的文学内功,并让人憧憬作者的可能性。
就在那几年,同样生长于沈阳的“80后”作家双雪涛和郑执,也因为对父辈一代的书写受到瞩目,他们与班宇一起被并称为“铁西三剑客”,或是“东北文艺复兴三杰”。
李陀说,这些年轻作家不约而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他们一起努力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潮流,这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当代文学该出现一个新格局了”。
直到今天,班宇小说的设定与腔调出奇一致,他常常从当下起笔,溯洄埋藏在过去的伤痕,驰骋他富有辨识度的语言,由此形成鲜明的风格。他也赞赏萨莉·鲁尼(爱尔兰作家,著有《聊天记录》《正常人》等)对当下现实的洞察和即时反应,但他依然希望将自己的笔托付给记忆和历史,站在时间之河的对岸,是令他更加心潮翻涌的位置。
“我的兴趣就是在旧的时代发现能映照出此刻和未来的那面镜子,这会让我特别兴奋。”班宇说。
时间
去年,班宇在北京待了大半年,作为文学策划参与剧集《扫毒风暴》。从前期筹备到全程跟组,对他来说,是一场艰辛的持久战。文学策划与编剧团队联系紧密,剧本会上经常提出一个问题:情节进展到这里,往下走有几种可能?作为尽责的剧组一员,班宇也一起敲着脑袋推演,但当他独自面对自己的小说,这种想法从来不会出现。
“小说永远只有一种可能,当某个地方可以有别的可能,说明前面哪个地方一定出了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像搭榫卯一样,细致搭建小说的结构,情节互相镶嵌,细节草蛇灰线,到最后,只能走向一条必然的路,这甚至不是作家能左右的。他尊重规律,也尊重命运。
班宇和影视的初次相遇,是为《漫长的季节》做文学策划。这部2023年播出的剧集,同样以东北工人下岗潮为时代背景,与班宇最早的那些小说不谋而合。导演辛爽以班宇一篇小说《漫长的季节》为剧集命名,剧中那首诗《漫长的》,也出自班宇之手。
剧组生活的密度和节奏极高,时间感会发生扭曲,班宇觉得剧组一天相当于日常三天。有时连续出四五个“大夜”,晚上七点出发,拍到早上五六点回来,睡一觉,十一点又开会。渐渐地,写小说的手痒了,他见缝插针写几段,写出一篇《清水心跳》,主角的身份就是编剧,开篇写道“在北京时,我睡得不好”,也是写实。
拍摄结束,他回到沈阳,时间流速回归正常。为了克服懒散,每天上午,他像上班一样去离家15分钟路程的工作小屋,听听唱片,下午看书、写作,晚上七八点回家。周末是陪女儿的时间,他带着女儿逛劳动公园、南湖公园,那是他小时候玩耍的地方,也是他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地标。
2022年年底出版的小说集《缓步》中,父亲与年幼女儿的组合进入他的笔下,新书的《狐及其友》里也有带着女儿的父亲。写着写着,他也觉得人物有些相似,但他从不畏惧自我重复,“即便有重复,但我是诚实地表达,没有用那些无聊的技巧,去编造奇观一样的故事,那不是我写小说的初衷”。人生走到此时,笔墨也行至此处,女儿自然而然出现在笔下。故事里写到女儿时,他的用笔总是掩饰不住地温柔起来。
铁西少年转眼长成慈爱的父亲。前几天,班宇梦到一个定居澳大利亚的故人,梦中回到他们的中学时代,放学后一起在路边小摊上买游戏光盘。一切都真实发生过,梦境也是记忆。梦醒后,他给朋友发了条信息,说竟然二十多年了。突然伤感不已。
“这二十年里,我们好像干了很多事,其实又什么都没干,时间却在不可遏制地一点点流逝。”班宇说,“我也不知道哪种生活是正确的,我甚至认为所有的生活都是错误的。”
他笔下人物,比比皆是在时间之河里浸湿的人。新作《清水心跳》里,作家与读者因为小说相遇,他们都被同一件往事纠缠,多年不得安眠,终于在一场长谈之后,走出了停滞的时间。就像《漫长的季节》里,说要“向前看,别回头”,但整部剧都在向后看。
“每次想到时间流逝,我都会特别难过。”他有些动情地说,“因为我特别爱这个世界。”班宇故事的底色都是惆怅,对时间流逝的敏感,是他惆怅性格的来源之一。唯有真心可以抵御伤感,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敢于付出真心的人,是《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是《逍遥游》里的许玲玲,是《白象》中的李小天,是《飞鸟与地下》中的小柳……他们在密不透风的灰霾中撕开一道裂隙,那是让生活重新赋予意义的唯一方式。
拍摄《漫长的季节》时,导演辛爽想法明确,不同于此前影视创作中对于东北冰天雪地、寒冷彻骨的刻板描绘,他想拍出明晃晃的东北秋天。剧情中的两段故事时隔二十年,都发生在秋天,当范伟饰演的王响解开命运的谜团,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落了下来。冬天到了,时间再次流动,那个困住他二十年的漫长的秋季,终于过完了。
这场大雪的灵感,取自班宇小说《冬泳》封面上的一句话:“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在另一篇中篇小说《渠潮》的尾声,他也用一场大雪收束全篇,那是他对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的致敬——“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每个人都有一场生命之雪。”班宇说,在《漫长的季节》里,那场雪对不同的人有各自的意味。但每个人都有那样一个时刻,像遭遇一场大雪一样,被彻底改变了命运。
这场雪一直在班宇的笔下飘落着。“《白象》里的那些人物,大家如果细心的话,也会找到那场雪飘落的时刻。”他说,那是《白象》中拼凑多年的真相终于和盘托出的时刻,是《关河令》中父子在火车站遇见又错失一次天启般翻身机会的时刻,也是《清水心跳》中从未谋面却因同一件往事无法安眠的两人终于可以睡去的时刻……
“出书特别像出唱片。”前乐评人班宇说,就像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或者万能青年旅店的《冀西南林路行》,整张唱片也是一首完整乐曲。班宇对小说集篇目的整齐度有近乎苛刻的执念,他从尚未结集的二十多篇小说中选出五篇,集合成《白象》,因为它们气质相通,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就是一篇小说。
这批作品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人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故事里大多有一个悬置在过去的谜。“我们今天再往前多回顾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你和家人的历史,与今天会产生剧烈的共振。”班宇说,“今天所有的困惑和不解,也许都能找到答案。”
班宇的语言密度极高,他举起锤子,将一个又一个细节砸实,挤出语言中的水分,密实地压缩在漫长的段落里。故事密不透风,只在一些抒情段落,读者可以换一口气,再接着沉入密集的叙事中。写到今天,他的段落还有越写越长的趋势,人物会一口气讲出五六页的篇幅,班宇说,他希望营造一种时间在叙述中流走的感觉,不希望被打断节奏。
以这种高密度叙事的手法,很难拓展出更长的篇幅。中篇《白象》是他最长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横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90年代多个时期,空间从上海到东北,他试图借这个题材拓宽写作的时空边界,一开始也想写得更长一些,然而即便如此广阔的内容,他用四万多字,也就写完了。
他执迷于密度带来的力度,句子之间有引力,如果抻得更长,引力就会松弛,结构的张力就会削弱。他不吝惜素材,没有要将故事养成长篇小说的执念,“长篇小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如果要写,我需要重新发明一种能让我使用的语言”。
班宇手机上没装短视频软件,但他很清楚,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被短视频和社交网络割碎到何等地步,在碎片化的世界里,短篇比长篇或许更符合时代气质。“今天写那么长干吗?除了让自己得到一点点爽感之外,真的考虑到文学审美和读者了吗?”他说。
作为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班宇的小说已经受到影视行业的关注,代表作《逍遥游》改编的电影正等待上映,多个改编电影和剧集项目也传出了消息。版权收入改善了作家的生活,2020年他从工作了十几年的出版社辞职,专职写作。但影视的青睐没有改变小说创作的质地,他甚至故意反抗,写了一些根本无法改编的小说,更先锋、更实验、更晦涩。
“我觉得为了改编而写小说,好像有点没出息。”班宇写作的初衷和乐趣,都在于文学本身。他从文字中发现了尚未被开拓的潜力,可以安放他对记忆、时间和人的感受,这带给他探索的诱惑。因而他至今的创作平稳而持续,频繁现身于文学期刊,每隔两年左右合为一本。
“小说自有它可以做到且只有小说能做到的事,比如给予人以真正的想象,比如读到沉重的命运,可以让人在阅读中能停下来喘口气。”班宇说,“我不认为小说是一个落后的形式,它仍然能让我兴奋。”
杂志标题:班宇:每个人都有一场生命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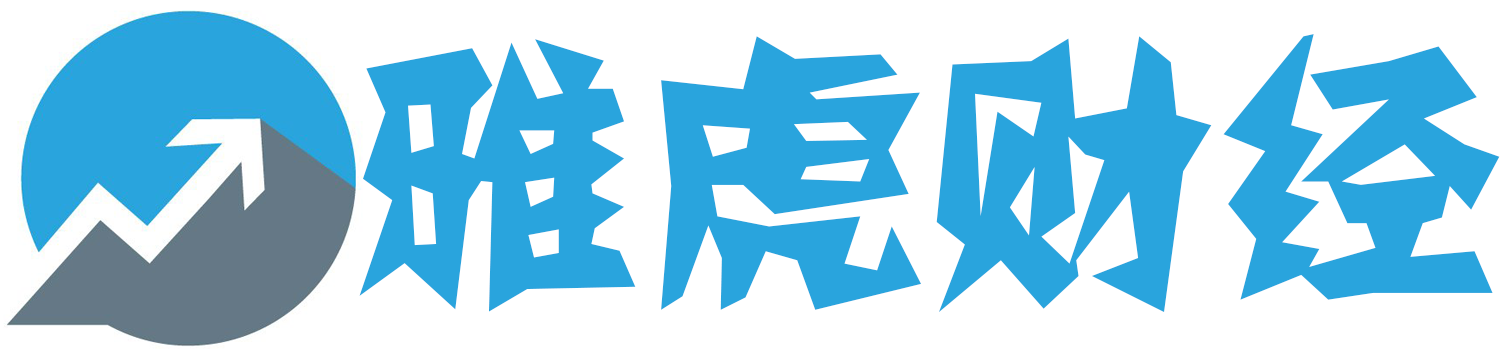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